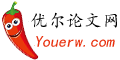自然辩证法学后感 第3页
摘 要:自然辩证法既保持了传统哲学追求智慧的形而上品格,又具有现代科学追求知识的形而下品格,是科技时代人类智慧的楷模;它既蕴涵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又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既关联人类的终极关怀,也关联着人类的现实关怀,对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它还是我们当前反对形形色色现代蒙昧主义,为全球化和现代化发展扫除精神障碍的思想武器。
关键词:自然辩证法;终极关怀;全球化;科学文化;现代蒙昧主义
早在自然辩证法从恩格斯头脑中的一种思想观念客观化为一个物质性文本时,当代哲学就已经在酝酿一个根本的转向。现代科学征服自然界就象我们的先民曾经驯养野生动物一样,整个自然界这头特大的猛兽在科学家有条不紊的驯服操作中变得越来越温顺、越来越容易驾驭。这里似乎再也没有哲学家夸夸其谈的任何余地了。拒斥形而上学开始走出科学的领域成为哲学的一种自觉思想和行为。形形色色的当代哲学几乎不约而同地栖身于语言之中寻求新的出路和发展,结果不是飘泊在“人文”队伍中继续夸夸其谈,就是沦落到“科学”行列中蜕变为一种普通专业。然而恩格斯却仿佛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他在对科学的发展表示欢欣鼓舞的同时依然以一个哲学家的身份继续审视自然界,并且迫使兵临城下的现代科学为哲学留下一块地盘。尽管恩格斯的冒天下之大不韪受到转向以后当代哲学的诸多非议与指责,然而当前人类思想文化的相对主义走势则开始显示出,这种根源于科学与人文之间的自然辩证法蕴涵一种可以作为中流砥柱的当代价值。
1
恩格斯所生活的年代,历史已经进入了科学时代。黑格尔思辨哲学体系不可避免地衰落,曾引发了一场深刻的哲学危机。拒斥形而上学、建构一种符合时代精神的新哲学,已经成为历史赋予那个时代哲学家的重要使命。恩格斯既反对那种独立于实验科学之外、却又试图凌驾于实验科学之上的、作为“科学的科学”的思辨哲学,也反对那种将实验科学拔高为哲学的哲学,更反对那种将哲学物化为实验科学的哲学。自然辩证法正是他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对于传统哲学危机所作出的一种现代回应。从恩格斯同时代的各种哲学在当代的发展演变来看,自然辩证法无疑堪称科学时代人类智慧的一种楷模。
第一,自然辩证法作为一个尚未完成的文本,蕴涵着科学时代人类所特有的睿智,它准确地勾画了科学时代自然哲学应当具备的基本框架,从而使得以哲学的面目出现的自然辩证法可能成为科学时代真正科学的哲学。首先,自然辩证法继续保持了传统哲学追求智慧的形而上的品格,这就使得它截然不同于以拒斥形而上学著称的新老实证主义哲学。恩格斯反对超自然的形而上学,然而他并不一概反对“自然的形而上学”,他没有以知识完全消解智慧,而是创造性地保留了哲学作为智慧之学的独立地位。这一点集中体现在自然辩证法的世界观属性上。尽管现代科学已详细描绘了自然界的许多局部细节,惠威尔已提出了独立的科学概念,休厄尔则以物理学家取代了自然哲学家,然而科学的世界观关于物质世界的理性重建,并不是由物理学家所能够独立完成的,它必须由熟悉全部自然科学的哲学家进行全面总结和概括;其次,自然辩证法同时具有现代科学追求知识的形而下的品格,这又使得它截然不同于以智慧的化身自居的形形色色反科学主义哲学。恩格斯非常注重智慧与知识的内在关联,从而得以避免了极端的人文主义以虚妄的智慧贬损知识的蒙昧主义倾向。自然辩证法作为“自然界的辩证法”,虽然它在形式上超越了自然科学,然而其内容却又完全根源于自然科学;再次,自然辩证法不仅是一种科学的自然观与世界观,而且同时主要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它作为关于自然界的一种科学的哲学,不仅能够促进大量边缘学科与交叉科学的发展,而且可以推动着现代横断学科和统一科学的发展。它的那种建立在通晓迄今为止人类全部科学知识基础上的科学思文方式,可以给自然科学各门不同的学科以方法论方面的智慧启迪,而这无疑是作为一种哲学的自然辩证法之所以能够受到许多科学家欢迎的内在原因。
第二,自然辩证法作为一种崇尚智慧的哲学,是以科学作为蓝本建构起来的,自觉与科学结盟是自然辩证法的一个重要特征,尊重科学、尊重事实始终都是自然辩证法的一项基本原则。首先,恩格斯当时已经明确意识到,随着自然科学关于自然界各个局部领域实验研究的不断扩展和相继独立,哲学只剩下了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 [1]。这样的哲学倘若还要有所作为,它或者是走向科学和理性,或者是走向宗教与信仰,或者走向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恩格斯显然选择了与科学结盟;其次,自然辩证法虽然保留了哲学的世界观职能,然而这种世界观是按照科学的结论所建构起来的科学的世界观,它是建立在总结和概括全部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的。在恩格斯看来,现代哲学只能是为科学的世界观提供辩证法这样一种全新的理论思文形式,而自然辩证法关于自然界存在方式和演化发展的辩证观点则必须根据自然科学所获得的辩证结论进行总结和概括。同科学时代相适应的世界观只能是这种科学的世界观,而与此同时这种作为世界观的辩证哲学也全然不同于传统的以经验为蓝本的世界观哲学了;再次,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原因,这种科学的哲学就必须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地改变自己的形式。由此可见,这种作为世界观的辩证法,并不像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从自然界的外部简单地注入自然界的。辩证法在作为哲学家的恩格斯头脑中固然是外在于科学的,然而在作为自然科学最新进展的星云假说、生物进化论和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等最新的科学理论中,则显然是内在于科学的。如果说它是被从外部注入自然界的,首先把它们注入自然界的也是自然科学家而不是作为哲学家的恩格斯,尽管恩格斯具有这样的预期。
第三,自然辩证法辩证地综合了实在论传统中的哲学真理和根源于唯名论传统中的科学真理,妥善地解决了哲学中的绝对真理与科学中的相对真理的关系,从而既反对了真理观上的绝对主义,也避免了真理观上的相对主义,它对于当代人类思想文化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恩格斯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从柏拉图到黑格尔为止的传统自然哲学追求绝对真理的虚妄,然而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绝对真理,而是把它直接同科学认识联系在一起;其次,作为一个哲学家,恩格斯也清醒地意识到了科学真理的暂时性与相对性,然而他也没有因此而贬低科学真理,而是借助于哲学真理去为它构筑绝对的基础;再次,恩格斯把直觉的、感悟的、绝对的和虚无缥缈的哲学真理与逻辑的、语义的、相对的、然而却确实可靠的科学真理辩证地结合在一起,坚持和捍卫客观真理,不仅充分地体现了哲学家所特有的智慧,而且对于迷失在语言的世界中找不到北的当代哲学具有一种指南针的价值。许多人追随西方马克思主义因此把自然辩证法指责为自然本体论,这实际上是对恩格斯的一种误解。尽管自然辩证法文本中确实没有对自然界的属人本性予以明确界定,然而事实上恩格斯早年所著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已明确批评过法国唯物主义的自然本体论,说它们“把自然当成一种绝对的东西来代替基督教的上帝,并把它和人类对立起来”[2],这说明恩格斯早就达到了人化自然的认识。由此看来,在自然辩证法这样一部以总结和概括自然科学结论为主体的、尚未完成的遗稿中没有对自然界作出具体的界定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2
自然辩证法既然是一种科学时代的人类智慧,是科学的世界观,它必然要给人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以科学的影响。当代哲学中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理性主义曾积极致力于发展一种科学的人生观与价值观,然而僵硬的实证主义哲学立场和纯粹的认识论取向使他们的研究纲领不仅在理论上困难重重,而且尤其疏远了现实的人生。实证主义衰落后,以非理性为特征的人文主义哲学主导了世界观领域,人生观和价值观问题几乎成了科学的禁区。在某些极端的人文主义者看来,科学与理性不仅于人类无益,而且简直是一个残害人类的恶魔,只有宗教和神秘主义才能够为人类带来福音。这种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实践上是有害的,而且尤其对于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非常可怕。事实上,自然辩证法处处以它特有的科学精神深切地关注并内在地关联着人类的终极关怀。
第一,自然辩证法不仅描绘了一种科学的世界观,而且内在地蕴涵着科学的人生观。这不仅具体地体现在恩格斯从宏观上把人类置于生物进化的序列之中,以劳动来解释从猿到人的转变,而且具体地体现在恩格斯还主张以化学的途径从微观上说明人类的起源;换句话说,体现在自然辩证法理论所特有的科学态度和理性精神上。具体说来,一方面人生并不是不可以加以分析的,事实上,不仅是现代生物学把人的身体分析到分子层面,而且现代心理学还把人的精神分析到了无意识层面;另一方面,从人格的三部结构来看,尽管是知、情、意同时主宰着人生,然而真正属于人的现实的人生却只能是以认知作为基础的人生。非理性的意志不仅是盲目的,而且是非人的,既然它不能够把人从动物中真正地提升出来,自然是谈不上什么人的尊严;而非理性的情感则不仅是自私的,而且是野蛮的,文护施情者的尊严,必然要亵渎被施情者的尊严,除非我们在认知的基础上达成两情相悦这样一项理性的原则。事实上,不仅是科学的人生观以科学的认知为基础,前科学的人生观也仍然是以朴素的认知作为基础的。人生观与科学绝非某些人文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互不相关。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时期,为了解放人们深受传统文化压抑着的精神和本能,以科学认知为核心的理性文化来更新传统的以宗教教义为核心的宗教文化,确保人的知、情、意三者之间的平衡,适当张扬被陈腐的认知过分约束了的人的情感、意志,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然而一厢情愿地把人的自由意志膨胀到了极端,以至从理论上完全无视科学理性,或者根本否定了客观规律,似乎只有蒙着眼睛自欺欺人的人生观才能够具有魅力和意义,这种观点显然是非常荒谬的。
第二,自然辩证法作为一种科学的哲学,也内在地蕴涵一种科学的价值观。价值观从来都是众说纷纭、千奇百怪,而所谓科学的价值观主张以科学的态度分析和评估人与世界之间的各种价值关系,其中包括人与世界之间的认知价值关系。近代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不断扩展,传统哲学日趋萎缩。哲学家为了给自己保留最后一块地盘,悍然切断科学与价值的内在关联,剥离科学的人文属性,千方百计将实事求是的科学限定在事实领域中。然而这一切并不能阻挡科学前进的步伐。实际上,事实与价值都是根源于同一人类主体的社会实践活动、反映人与世界关系的内在统一的两个方面,它们都需要接受人类科学思文方式的分析和评估。把科学与事实捆绑在一起,而把价值拱手让给非科学,势必造成人类主体的多重分裂。事实上,科学从来都不是价值中立的,它总是要致力于按照自己的内在逻辑在各种价值之间进行评价和选择。为了全面抵制科学向价值领域的渗透和扩张,现代反科学主义避开科学对价值的批判围魏救赵,它们炮制出一系列所谓自然价值、生态伦理、动物权利等抽象的价值,并以此为基础猛烈地抨击科学。它们把科学描绘成一柄双刃剑,谴责科学将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其实科学作为一种寻求确实可靠的知识的意识形式,同人类的宗教、道德、艺术、哲学、政治和军事等意识形式与社会活动相比,没有任何负面价值。价值根源于人类的实践活动,而支配人的实践活动的,恰恰是根源于人们那颗非科学的心灵深处某种非理性的盲目冲动,人类的所有灾难都是由于非科学的价值凌驾于科学之上产生的。恩格斯曾警告人类不要过分陶醉于对于自然界的胜利,其批判的矛头所向是人类的功利主义而不是自然科学,隐藏在形形色色全球问题背后的是各种各样的功利主义而不是科学主义。
第三,自然辩证法把人类的伦理道德带到了科学的境界中。这不仅是具体地体现在恩格斯曾经以发展的观点详细地揭示了人类伦理道德的社会历史起源,而且更重要的还体现在他是以科学的观点具体和现实地考察人的本质的。传统伦理道德由于没有科学地解决人的本质问题,因而总是要以某种莫须有的抽象的人性作为基础,在想象的世界中思辨地建构道德形而上学的空中楼阁。这种反人类和非人性的伦理道德一旦借助于宗教和政治的力量加以社会化,必然酿成人类巨大和持久的道德灾难。自然辩证法把人类的伦理道德从形而上的标语口号式的语词境界带到形而下的感性具体的图像境界中,把善严格建立在“真”的可操作的基础之上。它一方面充分尊重个人的各种本能需求,另一方面又把个人需求的现实满足建立在不能危害到他人的前提之上。这种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契约式的伦理道德不仅较之各种宗教以编织谎言、实施恐吓和信口许诺来世幸福为基础的伦理道德要高尚,而且较之中国历代儒家以抽象人性为基础的伦理道德更高尚,前者巧妙地掩饰了人的自私,后者则赤裸裸地鼓励和繁殖了人的虚伪。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通常习惯于空谈哲学境界,而根本否认科学境界,这是一个极为可怕的偏见。实际上,现代科学不仅在微观和宇观两极领域里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物质世界,而且还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精神世界,从而使人们的思想不仅能够真实地延伸到遥远的宇宙空间自由翱翔,而且可以沉浸在更为细腻、更加丰富的灵魂深处尽情漫游。
3
自然辩证法作为一部未完成稿,包含着相当丰富的内容。它不仅是作为科学的哲学,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极为抽象的层面上深刻地关联着人类的终极关怀,而且还从科学、技术、经济与社会发展等非常具体的层面上倾注了恩格斯对于人类极为浓厚的现实关怀。恩格斯在撰写自然辩证法的过程中不仅广泛地涉猎了当时的自然科学,而且在他留下来的未完成的自然辩证法手稿中也包含了大量有关自然科学的论述,其中不乏一些真知灼见。这些零散的内容已经被许多学者进一步发挥成为系统的科学技术观或者科学技术论,它们对于人们理性地解决当前所面临的许多重大社会现实问题具有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作用,从而又不妨被作为科学时代的科学技术学原理。
第一,自然辩证法科学地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从而可以为人类自身的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伴随着全球问题的提出而为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由此引发了宗教和各种带有浓厚宗教神学色彩的抽象空洞的反人类中心主义喧嚣。只是人类中心主义绝非其诽谤者所想象的那么脆弱,它作为人类安身立命的根本,不仅在人类自身发展壮大的实践中颠扑不破,而且在认识论和价值观等纯理论层面上也不可能受到真正的反驳。事实上早在恩格斯撰写自然辩证法的时候,就已经深刻地反思过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人类作为自然界发展的产物,无疑应当充分尊重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和自然界发展的客观规律,倘若幻想以这种作为人类认识结果的客观规律和自然界的优先地位来挑战人类中心主义,则显然是十分荒谬的。海德格尔把人类想象成为存在的看护者,环境伦理学家则主张“众生平等”,某些极端的反人类中心主义者强烈反对人类征服自然,恶毒攻击人类是“地球肌体上的癌细胞”,把人类看成是“大自然的错误,是大自然不幸的产物”[3],似乎只有退化为动物的人类才是真正的人类,甚至唯有没有人的地球才是一个健康的地球,这已经完全堕落为一种赤裸裸的蒙昧主义。至于当前某些所谓的文化人在后现代文化相对主义语境中舍近求远,热衷于鼓噪的所谓“天人合一”,也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蒙昧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是天命、天道、天理的意思,而决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宇宙或自然,所谓“天人合一”,是儒家关于天命合于人性、天道存于人心的一种本体论阐释,同现代所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风马牛不相及。它不仅无力解决全球的生态问题,而且也丝毫无益于解决当前中国自己的发展问题。要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不应当、也不可能指望回归宗教或玄学,而只能依靠发展科学;人类不可能、也不愿意象某些浪漫主义者憧憬的那样重新复归于子虚乌有的所谓诗意自然,而只有进一步深化人类对包括自身在内的自然界和自然规律的科学认识,才能真正为人类自身创造一个更加美好和实实在在的物质和精神家园。一切蛊惑人心的标语口号和歪理邪说在这里都丝毫无济于事。
第二,自然辩证法以现代全新的自然观作为思想基础内在地蕴涵了一种新的科学的发展观,它一方面要求科学、技术、经济与社会之间横向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则要求当代人与其子孙后代之间纵向的可持续性发展,从而为我们当代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具体的思路。全球问题的提出,不仅凸现了人类自然观层面上的种种形而上学反思,而且引发了一系列社会文明观层面上的哲学问题。浪漫主义者义愤填膺地谴责和声讨工业文明,形而上学家则别出心裁地炮制出所谓“生态文明”以取代工业文明,而问题的关键却在于,全盘否定工业文明后的所谓生态文明将会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文明,当这样的文明可持续时人类自身是否还可以“持续”?浪漫主义者固然可以不考虑这些问题,而为浪漫主义者所代表的人类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不予考虑的。实际上,所谓的生态文明充其量只能是作为文明的一种属性,用以标志一种文明的理想及其发展的高级阶段,而不可能成为文明的实体,从而也就很难成为一种独立的文明类型。其实无论是工业文明,还是农业文明以至人类最为原始的狩猎文明,其中都有一个生态问题,只是由于前现代时期人力尚小不足以破坏生态平衡、感受到生态危机而已。天真地想象一种抽象的生态文明,并把它同现代工业文明绝对地对立起来,鼓吹什么“零增长”甚至于“反科技”,只能是把人类引向一场新的、更大的灾难。
第三,自然辩证法客观地阐明了科学技术的性质及其社会地位与作用,对我们正确认识当代反科技浪潮,制定积极稳妥的科技发展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科学技术是人类能动地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智慧结晶,也是人类彻底摆脱动物界、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根本标志,是人类自己解放自己的伟大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对科学技术的任何新的发展总是欢欣鼓舞,尽管他们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应用也时刻保持着高度地警觉。现代科学技术不仅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物质文明的昌盛与精神文明的进步,而且推动着社会经济结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巨大变革,涤荡着一切腐朽的生活方式、意识形式与社会结构,从而必然要受到寄生在传统社会中的宗教神学、荒诞玄学和陈腐儒学等各种既得利益学科的从业者及其痴迷者与追随者的诬蔑和抵制。现代反科技思潮作为旧的意识形式的思想残余,以全球问题作为突破口恶毒攻击所谓“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显然是别有用心的。形形色色的全球问题固然同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密切相关,然而它完全属于人类自身进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其本质是科学技术的社会操作无范或失范的问题,症结并不在科学技术本身。把这样两个性质绝然不同的问题蓄意混淆起来,因噎废食,目的无非是想恢复曾经“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教神学、荒诞玄学或陈腐儒学。事实上,解铃还需系铃人,早已腐朽不堪的传统意识形式过去无能、现在无力、今后就更不可能面对扑朔迷离的现实,真正解决全球问题的绿色意识与环保策略只能是来自于现代科学和其中内在蕴涵着的人文关怀,前现代传统文化中的一切豪言壮语在这里都只能是相形见拙。
4
当代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时期,它绝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时间概念,同时还包含着十分沉重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是贯穿着现代世界历史的一条主线,在当代不仅体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生存对立,体现为人与人、集团与集团、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还体现为个人与社会、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日趋激烈的思想文化斗争。科学与反科学正是这一系列矛盾和斗争的焦点。文明的对立和利益的冲突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呈现出一种异常紧张的后现代格局,使表面上相对平静的当代世界,内在地潜伏着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危机。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自然辩证法将有助于我们顺利地克服这些危机,成功地开创一个光辉灿烂的明天。
第一,自然辩证法内在地蕴涵一种同科技时代相适应的朝气蓬勃的精神文化,它是我们在后现代语境中重建人文理性的思想基础,也是我们当前创造先进文化的思想前提。首先,自然辩证法自觉地继承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高扬人的价值与科学价值的人文主义传统,其中人文与科学有机地融合为一个整体,不仅关联人类的终极关怀,而且关联着人类的现实关怀,尤其具有浓厚的理性精神,堪称一种真正科学的人文主义。相比之下,当代的玄学人文主义一方面惧怕和诅咒客观规律,极力反对和阻挠科学探索真正的自然规律,掩耳盗铃,沉浸在自由意志的无限膨胀中自我陶醉,另一方面又热衷于信口编织和杜撰宇宙的意志和规律,张扬蒙昧主义垃圾,到处散发一股颓废腐朽的晦气。恩格斯撰写自然辩证法的年代,资本主义从科技革命中注入了新的动力并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战争的阴云开始笼罩了整个欧洲。然而恩格斯既没有像尼采、布克哈特、哈代和法朗士等“世纪末”思想家那样,否定以科学为基础的现代文明,回到个人内心世界,也没有像贝尔纳、海克尔、安捷尔等新启蒙思想家那样对未来盲目的乐观。他在对科学的发展表示欢欣鼓舞的同时,也对乐观主义者的自我陶醉提出了智者的警告。自然辩证法到处渗透着恩格斯浓厚的人文关怀与科学精神;其次,自然辩证法所特有的哲学观、科学观、真理观与价值观对于迷失在语言和逻辑世界中的后现代相对主义思想文化根本摆脱困境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迪;再次,自然辩证法同科学技术联盟为未来哲学理性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客观的理性基础和稳定的经验基础,避免了哲学以理性的名义把人们引向非理性信仰的歧途。现代哲学已基本上失去了自己的地盘,它们不是仰慕科学使自己专业化为一门思文的技术,就是崇尚清谈、故弄玄虚、花言巧语、骇人听闻,再就是追随宗教使自己重新沦为神学的婢女。自然辩证法与科学技术的联盟不仅使它能够发扬哲学思文的终极性和无限性优势,为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作出智者的规划,而且还可以使它获得科学技术特有的批判理性,从而对哲学的高谈阔论、危言耸听提出理性的质疑。
第二,自然辩证法可以为世界历史的全球化运动提供理性的辩护。首先从学理上看,自然辩证法把社会发展理解为一种物质运动并把它纳入自然界的物质运动系列来考察,不仅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思想,而且还为全面理解与深刻把握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提供了自然史方面广阔的知识背景和深厚的思想基础。全球化是世界历史这一范畴的内在逻辑必然,也是世界历史这一范畴的客观历史事实。它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运动。全球化能够涤荡传统文化中的污泥浊水,去伪存真,使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民族优秀的文化精神发扬光大。马克思所向往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必须通过全球化运动才能够最终实现;其次从方法上看,自然辩证法把社会运动理解为一种建立在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和生命运动基础上的高级运动形式,也为我们全面理解与深刻把握世界历史的发生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再次,从历史上看,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本身其实就已经是全球化运动的产物。欧洲的文艺复兴揭开了世界历史的序幕,它既是向希腊文化的一种回归,也是东西方文化的一种融合。文艺复兴以后的所谓欧洲思想,都不同程度地带有阿拉伯、印度与中国的东方印记[4]。自然辩证法思想在黑格尔等前辈思想家那里,就已经不是纯粹西方的思想,恩格斯在阐述自然辩证法时也常常提到东方的智慧。其实中国人所以比较容易接受外来的自然辩证法,也正是因为其中融合了中国自己的文化精神。把全球化同文化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不过是宗教原教旨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的一种阴谋。自然辩证法所具有的世界观与世界历史意识将有助于我们理性地把握当代社会,自觉地投身到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之中。中国的自然辩证法无论是作为理论、学科、还是事业,它同科学技术的自觉结盟,不仅内在地体现了全球化时代的时代精神,而且也提供了对全球化运动的理性辩护。正是因为具有这样一种独特的身份,使得它曾经在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启蒙和先导作用。
第三,自然辩证法是我们当前反对形形色色现代蒙昧主义、为全球化和现代化发展扫除精神障碍的思想武器。首先,自然辩证法是认识和把握当代风起云涌的反科技浪潮的理性基础。反科技是现代蒙昧主义的集中表现。一般说来,绝大多数反科技人士并不具体地反对物理学、化学或某一门传统的科学技术,而是反对科学技术向他们自身研究领域的扩展,确切地说是反对他们所不熟悉的科学方法,他们通常喜欢以反科学主义者自居。不过倘若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反科学主义事实上就是反科学。因为科学除了作为一个集合名词指称自然科学各门具体学科外,主要还是用来指称一种不同于传统宗教和哲学的意识形式、思文方式和思想方法。当代反科技人士主要来源于两个群体:一个是宗教原教旨主义,一个是玄学人文主义。从前一个群体看,科学与反科学的对立是科学与宗教对立的当代表现;从后一个群体来看,科学与反科学的对立则是科学与玄学对立的当代表现。无论是来自哪个群体,他们都必然要以蒙昧主义来反对现代科技;其次,自然辩证法是我们弘扬科学精神,反对愚昧迷信和伪科学的方法论依据。伪科学的实质也是反科学,它是反现代思潮的一种极为阴险的形式。恩格斯生前曾无情揭露和讽刺过克鲁克斯和华莱士在神灵世界中建构的自然科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自然辩证法同人坚持不懈地揭露和批判各种以神秘主义为特征的伪科学,体现了自然辩证法战无不胜的理性智慧和思想威力;再次,自然辩证法也是我们批判和抵制当前正在全球范围内肆虐蔓延的以极端民族主义为特征的反全球化逆流的理论基础。受文化相对主义蛊惑,一些腐而不朽的文化传统又死灰复燃。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宣称“21世纪是中国的”,某著名的博士生导师甚至要求他学机械的博士生必须背诵《老子》和《论语》。无独有偶,印度的右派走得更远,他们不仅疯狂叫嚣21世纪是“印度人的世纪”,而且断然宣布现代科学是西方的种族科学,印度人民党甚至还把所谓“吠陀数学”列为小学必修课,新的历史教科书则极力颂扬包括世袭的等级制度在内的所有印度传统,鼓吹印度神话是“雅利安民族”的原始家园,他们对包括穆斯林信徒在内的所有“外国人”表示悲哀[5]。事实上,文化最终还是生活方式的体现。未来以跨国公司和互联网为基础的生活方式选择的只能是建立在现代科技基础上的科技文化或世界文化,而绝不可能是“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农耕文化。全球化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自然辩证法与科学技术的天然结盟及其科学文化意蕴,有助于我们顺利跨越传统文化为现代社会可能设置的种种羁绊。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3.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97.
[3] 转引自陈昌曙.哲学视野中的可持续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01.
[4] 有关内容参见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5] 索卡尔等著.蔡仲等译.“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207-218.
[6]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7] 恩格斯.反杜林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
[8] 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1950.
[9] 赵修义、童世骏.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西方哲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本文原载《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4年第1期)
上一页 [1] [2] [3]
自然辩证法学后感 第3页下载如图片无法显示或论文不完整,请联系qq7520187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