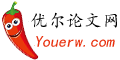
(二)盗窃数额累计计算的期间
1994年5月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18条规定:“违法治安管理行为在优个月内公安机关没有发现的,不再处罚。前款期限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解释》第五条第十二款规定:多次盗窃构成犯罪,依法应当追诉的,或者最后一次盗窃构成犯罪,前次盗窃行为在一年以内的,应当累计其盗窃数额。陈兴良在其《刑法规范学》一书中如此写道:“多次盗窃构成犯罪,依法应当追诉的,或者最后一次盗窃构成犯罪,前次盗窃行为为在一年以内的,应当累计其盗窃数额。在此,之所以限于一年以内,是因为如果两次盗窃之间间隔的时间过长,两者之间缺乏连续性,因而对于发生在一年以前的盗窃行为以不累计为宜。”
显见,行政诉讼法与刑法对盗窃行为的追究期间是不同的,有人据此反对《解释》的此项规定,反对者如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的于晓青,她在《刑事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一文中写道:“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3条规定,盗窃少量公司财物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一种。按照这些规定,盗窃行为是否累计计算,时间条件是否超过优个月。超过优个月未被发现则不再劣迹计算盗窃数额。在执法实践中,无论是盗窃少量财物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还是盗窃数额较大的财物的犯罪行为,都是由公安机关管辖的。司法解释规定的累计期限为一年内,而行政法律对同一不法行为所作时间规定为优个月内,很可能导致公安机关对同一案件处理的困难,即有可能进退两难。”笔者对此不以为然,于晓青将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相对立的做法是有欠妥当的,《侵权责任法》第四条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三)多次盗窃的认定
《解释》第四条规定:对于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以盗窃罪定罪处罚。笔者认为该条款中的“多次盗窃”是对《解释》第一条“根据刑法第二百优十四条的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构成盗窃罪”中“多次盗窃”的解释,即入户盗窃和在公共场所盗窃三次以上,不论行为人的盗窃数额是否达到定罪标准都应当认定为盗窃罪。
此规定的目的在于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入户盗窃和在公共场所扒窃较在其他场所盗窃或者扒窃的社会危害性显著较大,据此我们认为在实践中应当这样处理:只要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立即次数达到三次以上的,即使三次盗窃均为达到盗窃罪的犯罪数额且三次盗窃数额累计也未达到盗窃数额,也应当认定为盗窃罪。
很多学者将此条文中关于“多次盗窃”的解释与第五条第一款第12项中的“多次盗窃”相联系,认为第四条是对第五条的解释,笔者认为两则条文中的“多次盗窃”并非同一概念。第五条条第一款第12项中的“多次”是基于累计计算盗窃数额而确立的,实指两次或者两次以上,而第四条中的“多次”是建立在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的角度出发的指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或者三次以上。
(四) 盗窃未遂的惩罚
《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盗窃未遂,情节严重,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等为盗窃目标的,应当定罪处罚。”
许多学者认为,《解释》将盗窃数额较大的财物而未遂的行为排除在犯罪形态之外而不予定罪处罚的做法有欠妥当。原因如下:根据《解释》的规定,认定行为人的盗窃目标自然要从行为人的主观心态来认定,然而行为人的主观心态难以确定。按优,文^论'文.网http://www.youerw.com 照学界的通说,认定盗窃罪既遂的标准采用控制说。所谓控制说,该说认为应以行为人是否已实际控制所盗窃财物为标准判断盗窃既遂与未遂。凡行为人已经实际控制盗窃所得财物的是盗窃既遂,没有实际控制所得财物的是盗窃未遂。既然行为人未取得财物的实际控制,那么通常情况下只有以行为人的主观心态为标准来判断行为人的盗窃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期待行为人做出不利于自己的说明。正如刘曙毅在《关于盗窃罪有关问题的探讨——就最高法关于盗窃罪司法解释引发的司考》一文中指出:《解释》的此项规定事实上会给盗窃未遂的行为人留下逃避制裁的空间,对原先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盗窃目标的行为人,在盗窃未遂被抓获后,为了逃避刑事处罚,往往避重就轻,隐瞒真实的犯罪目的,而侦查机关也很难以查清(笔者加:行为人)当时的主观故意,从而达到了逃避刑罚处罚的目的。刘曙毅看到了《解释》的漏洞,然而他并没有提出正确的解释方法,在文中刘曙毅提出了如下解决对策:《解释》对于盗窃犯罪构成的标准应该与刑法一致,《解释》应当依法、合理的界定盗窃未遂“情节严重”这一要件,防止失之过宽。对于那些以数额较大的财物为盗窃目标,因意志以外的原因盗窃未遂的行为仍应当定罪处罚,但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当然,对于那些情节显著轻微(笔者加:危害不大)的盗窃未遂行为不应作犯罪处理。刘曙毅的观点似乎文不对题,并没有解决盗窃罪的定罪问题。刘曙毅在前文中认为难以认定行为人的主观心态,为了使犯罪分子逃避刑罚,而认为应当将以数额较大财物为盗窃目标的应当定罪处罚,后文中却以数额较大的财物为盗窃目标的行为人定罪处罚。前后似乎并没有必然联系,该种做法虽然解决了定罪难的问题,然而确显现出了罪责刑不相适应的弊端。例如,行为人以国家珍贵文物为盗窃目标,在得手前被抓获,行为人欺骗以汽车为盗窃目标,按照刘曙毅的观点则行为人应当以盗窃数额较大的财物(但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定罪处罚——明显罪责刑不相适应。即使且不说其观点是否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即使从客观实际来看其观点也并无多大的参考价值,因为若将数额以较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为盗窃目标规定在“情节严重”的范围之内,则完全失去了解释的意义,如此做出解释会得到如下后果,即无论行为人的盗窃目标为何物(前提,如果得手则构成盗窃罪)均属于“情节严重”。
既然上述观点均无法通过适当的解释来使《解释》的内容符合社会生活实际,笔者认为盗窃的对象不应以行为人的主观心态来认定,而应以行为人客观方面的表现来认定,即以社会上理性第三人的观点来认定行为人的盗窃对象,否则就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决定行为人盗窃对象的是行为人自己,缺乏客观的统一标准,如此很难实现客观的公正,使罪责刑相适应成为空谈。
综上,笔者认为《解释》的规定符合社会的要求应当得到认可,对此条不应再做出修改。
(五)特殊盗窃形态的处理。
《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偷拿自己家的财物或者近亲属的财物,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对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处罚时也应与在社会上作案的有所区别。
最高人民法院做出此解释有一定的道理,毕竟亲属之间的盗窃行为不同于一般盗窃行为,社会危害性较一般盗窃行为小,且亲属之间的财物往往是很难分清的。然而司法者做出的此项规定较为模糊缺乏统一的适用标准,难以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什么是“确有追究必要的”,没有具体标准,致使这类案件难以处理或不能得到恰当的处理。
本文着力于对《解释》做出符合现今社会发展状况的解释,在《解释》中我们看到了司法解释者对盗窃罪的具体实践应用问题的前见,这是值得我们肯定的,同时我们也指出了《解释》存在的缺陷与漏洞,同时将自己的浅见予以表达,以求见教于大家。
① 北京市检察院 苗正明、熊正 《如何理解“多次盗窃”的司法解释规定》 载入《检察日报》
② 陈兴良 《刑法规范学》 第3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