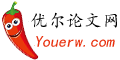
武松杀人后欲投奔杨志、鲁智深,路过蜈蚣岭见“一先生楼着一个妇女,在那窗前看月戏笑。”武松心想“山间林下出家人,却做出这等勾当”,便要拿他试刀。武松打开门看见一个道童出来,武松就先拿了“鸟道童祭刀”。随后武松又与王道人斗了几十个回合,砍下了作恶道人的头颅。王道人杀害了张太公一家数口性命,还强骗里张太公女儿,但是问题在于杀人后才问起缘由,也并非真正英雄之举,实属蛮横无礼。[12]
在对待复仇和正义的问题上,水浒英雄的行为确是可圈可点,复仇或是赚取同伙上山的同时,也使更多的无辜者殒命。从今天看来,人权中最重要的是生存权,若生存权都没有保障,社会就不会规范,百姓就不会愿望在这个社会中生活,礼仪规范就不会得到有效传播,同样,水浒英雄这种滥杀无辜的行为必须为他们日后的不得民心负有全部责任。
2.水浒英雄的“好淫杀”现象及残杀女性行为
水浒英雄“好淫杀”,在对待妇女,特别是“越轨”的妇女问题处理上十分残忍,野蛮。这虽然与古代中国妇女地位低下的历史背景有关,但与《水浒传》作者男权思想不无关系。
小说自二十四回起至二十优回大幅文字描写武松发现王婆、西门庆、潘金莲三人合伙杀了武大,武松请众邻吃酒,紧接着杀死潘金莲诸人的场面。武松“把刀月乞查了插了桌子上,勇左手揪住那妇人头鬟,右手劈胸提住,把桌子一脚踢翻了,隔桌子把这妇人轻轻提将过来,一跤放翻在灵床子上,两脚踏住”,然后“脑揪倒来,两只脚踏住他两只胳臂,扯开胸脯衣裳。说时迟,那时快,把尖刀去胸前一剜,口里衔着刀,双手去豁开胸脯,去除心肝五脏,供养在灵前”,又“月乞查一刀”,“便割下那妇人头来,血流满地” [13]。这是《水浒传》中最让人快意的一篇也是传颂的经典。不过从字里行间“血漉漉”的句子均可窥探到武松嫉恶如仇的本性,是何等的快意恩仇,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见武松对待妇女的极不人道。武松杀潘金莲的残忍行为可以视为整个社会“男尊女卑”的思想肆意的蔓延。这不只是《水浒传》的“好淫杀”,而是整个社会的“好淫杀”。古代法律就限定,捉奸如果捉双,可以当场杀死奸夫淫妇而不得到任何惩罚,因此可见封建社会人权的劣迹斑斑。
再如宋江为掩自己暗通梁山泊“打劫贼”,夺回招文袋,将与张三私通,受了恩惠还得寸进尺的阎婆惜杀死的情节:宋江“左手按住那婆娘,右手却早刀落,去那婆惜嗓子上只一勒,鲜血飞出,那妇人兀自吼哩”,“宋江怕她不死,再复一刀,那颗头伶伶仃仃落在枕头上” [14],孝义黑三郎之举可谓“义”杀阎婆媳,也算是真真切切的演示了《水浒传》的主题。
类似的事情《水浒传》中还有许多。好淫杀,杀淫女人最为恣意的是“杨雄大闹翠屏山”一段,石秀与杨雄商议让他假意约潘巧云约上翠屏山要问个缘由。实施之后将潘绑在树上,潘巧云吓坏了,要石秀劝一劝。石秀说:“哥哥自来服侍你。”那杨雄上前,“一刀便割了,且教那妇人叫不的”,把刀豁出了舌头。杨雄狠毒的骂道:“我想你这婆娘,心肝五脏怎地生的”,遂“一刀从潘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取出心肝五脏,挂在松树上”,而且“将这妇人七件事分开,却将头面衣服都拴在包裹里” [15],手法之毒,手段之残忍,令人不寒而栗。
又如李逵帮狄太公捉妖一回。在得知狄太公女儿与人通奸之后,李逵将两人“剁作十多段,丢在地下” [16]。李逵受人之托,“捉鬼”之后本该留下人的女儿便是,却将两人全部杀死且砍作十来段,可见此人手段之狠对人生命的藐视。
再如五十优回,张顺为救宋江连夜趱行,往建康请安道全。在得知安道全被一个建康烟花娼妓缠住,张顺又巧遇虔婆安排李巧奴与仇人张旺相会,“按不住火起”,“拿起厨刀先杀了虔婆,要杀使唤的丫环时,原来厨刀不甚快,砍了一个人,刀口早卷了,那两个正待要叫却好一把劈柴斧正在手边,正迎着张顺,手起斧落劈胸膛砍翻在地”,随后扯下衣襟蘸血写到“杀人者安道全也”[17]。安道全没有办法,只得上了梁山。李巧奴是烟花女子,本来出身命苦,只落得如此下场,连人带上虔婆三个人,张顺算是讲了义气,但是“一不杀少而杀众”,极不人道。
水浒英雄杀害妇女手段的残忍是任何其他小说不曾遇到的。种种残杀行为之下透着对于妇女地位的极大不尊重。男权思想和两性关系通过故事叙述和人物命运描写流露出来,思想是可惧的。这其中必然纠裹了传统腐朽文化的弊端,也包含着流氓文化的核心内容:成者王侯败者贼。这种推崇强者恃强凌弱的不堪观点。
(二)集体性“非英雄行为”和滥杀无辜行为
水浒英雄聚义之后几次展开了与庄院地主、州城府院的直接对抗和冲突。此类动作中有些是为了赚取英雄入伙,有些是为了解救受难的英雄,也有些为了解决山寨粮草问题。挑起冲突的主要方面是梁山团伙,在行动中也多有些莽撞行事,让百姓受了不少苦难。
仅仅在晁盖当上梁山统领的第二十四回中,义军大胜黄安。稍晚朱贵上山报“有十数人接连在一处,今夜晚间必从旱路经过” [18]。三阮请命下山,劫得财物二十余辆金银财物,这些不义之财与强盗动作无异,非正义之举。
再有三十四回宋江、花荣为了赚秦明入伙,叫小卒穿戴秦明衣冠,骑其马匹,执其兵器,攻打青州城。王矮虎领五十余人助战,杀人放火,断了秦明后路。结果把“数百人家烧成白地”,杀死男女不计其数,也害了秦明一家尽数被杀。宋江居然说:“兄长没了嫂嫂妇人,花知寨有一妹,宋江愿意主婚-与主管为室” [18]。如此的轻贱人命,怎么得民心。余象斗先生评价说:“宋江用此计顺秦明,此处见宋江不惜人之处,而可恨矣,而可恶矣。”
第四十八、四十九、五十回宋江带兵攻打祝家庄。宋江看见祝庄门上书“填平水泊擒晁盖,踏破梁山捉宋江”恼羞成怒。结果攻下祝家庄时,宋江命人将祝家庄洗荡了,只留钟离老人一家。李逵这个“梁山贼人”直抢入扈家院中,把扈太公一门老幼尽数杀了,不留一个,并让小喽罗将庄财赋“驼尽”。李逵请功时居然说:“虽然没了功劳,也吃我杀的痛快!”而顾大嫂“挚出两把刀,把应有妇人,一刀一个”。平心而论,拿杀人当作乐趣,这是梁山贼寇失败罪有应得的下场。
而第优十优回仅仅是为了赚取卢俊义上山坐把交椅,(卢俊义视梁山泊“那伙贼男女”,如同草芥),攻打大名府,使城内百姓黎民,“一个个鼠窜狼奔,一家家神号鬼哭,四十里处火光亘天,四方不辨” ,“民间被杀者五千余人,重伤者不计其数。” [19]紧接着,宋江、卢俊义攻打东平、东昌两府,目的仅仅是为了谁坐梁山的头把交椅,便以借钱为口号攻打城池,不惜黎民百姓受难。此回中宋江先攻打汶上县,目的是要百姓逃往东平府,以便让顾大嫂混在其中,去救史进,结果却连累了诸多百姓。他们扶老携幼赶往东平府,死伤不计其数。选谁做寨主的可笑决定都让诸多百姓受苦受难。这种以牺牲普通百姓的起义组织终将被人唾弃。
纵观中国历史上多次起义斗争,很多起义让中央政府头痛不已,但最后都是以失败结局。其中与滥杀无辜不无关系。一旦失去民心,组织严密的中央政府都可以瞬间瓦解,更何况是仅仅依靠义字连接在一起的义军。
(三) 招安后的残杀以及滥杀无辜行为
梁山集团也有达到辉煌胜利特别是两赢童贯,三败高俅之后,由于宋江本身受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中“三纲五常”的深刻影响,他完全接受了朝廷的招安。由此,英雄们走上了一条身不由己,违背自己初衷的道路。招安后的主要行动有:征辽、征田虎、征王庆、平方腊。
如果说征辽是使命为之,尚可配属爱国之心,那么征田虎、平方腊纯粹是起义军之间的残酷斗争。征田虎,攻太原市时久攻不下,竟然引智伯渠及晋水淹了太原,城中军民做了“水中鱼鳖”,“沉溺的,押杀的无数,尸骸顺流雍塞南城”,最后将田虎军士卒赶入陷坑中,军士以长枪乱罹,“可怜三千不留半个”。“其余人贼,都在威胜市实行斩首”。梁山集团残杀义军和百姓名分上是为了报销朝廷,终于皇帝,但是朝廷并未给他们任何好处,仍然没有得到皇帝的重用。而且不许入城。宋江不悟,竟然又接下大单:征方腊。
李逵趁入润州城,遭到守门官军的拦截,李逵抡起双斧,一砍一剁,早杀翻两个把门的军官。李逵为了替韩滔、彭圮报仇,李逵邀了鲍旭、项充、李兖四人冲杀南军,黑旋风“将高可立头缚在腰里,抡起两把板斧,不问天地,横身在里面砍杀,杀得一千人马退入城去,也杀了三四百人。”吕枢密说李逵是“梁山泊第一个惯杀人的好汉”,李逵再叫城时,“如箭穿雁,钩搭鱼鳃,默默无言,无人敢应” [20]。
在对待俘虏的问题上,梁山军队的作为也绝非人道。捉住敌军后,也是残忍到极点。如宋江破常州,命将范畴、沈抃、赵毅三人碎尸万段,枭首示众[21]。清溪洞一役宋江将杜微剖腹挖心祭奠秦明诸人[22]。
还有九十五回宋江智取宁海军,刘唐被砸成肉饼。李逵邀鲍旭、项充、李兖私人为刘唐报仇,将敌人副将斩于马下,但是鲍旭却被砍成两段。九十八回,宋江将南国伪官九十二人斩首示众。众英雄进入南宫中“杀尽嫔妃彩女,亲军御伺,皇亲国戚,都掳了方腊内功金帛”。直到最后“帮源洞中杀得尸横遍野,按《宋鉴》所载斩杀方腊蛮兵二万余级 [23]”。宋江传令“四下举火,监临烧毁宫殿,龙楼凤阁,内院深宫,珠轩翠屋,皆尽焚化”。[24]方腊也被运往北京,处以凌迟,剐了三日示众。[25]
三、起义军对“义”的理解和局限性
《水浒》中头领宋江身份十分要紧。小说中宋江智不及吴用、公孙胜,武比不上林冲、花荣,出身更是不及名震河北的卢俊义和豪门大户出身柴进,将校出身的关胜、秦明,却可以在梁山泊坐得头把交椅。其中与梁山集团内部对“义”的理解有重要关系。
梁山集团成员多出身于贫民,后又演化成流氓阶层。他们这种生活方式独立于正统的社会之外,因而正统社会中固有的伦常关系在梁山集团内部不再具有约束力,真正具有影响力的是以“义”为基础的集团内部的伦理观念。
梁山集团成员最初处在社会的最下层,他们必须为生存而学会劳动,天天野菜南瓜仅仅能够勉强度日。与此同时,他们必须依靠封建的正统伦理规则生存,必须承担抚养、赡养义务,必须效忠于皇帝而负担徭役、赋税的义务。在水泊集团中就不是这样,成员安于享受难得的自由和物品。他们重视朋友,因为只有朋友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的负担,甚至有时朋友还会伸以援助之手。比如鲁智深、林冲的友情只是为了一句赞赏;杨雄、石秀的友情在于危难中的彼此相互帮助等等,这些人可以为了朋友抛弃家庭,义无反顾。
可惜的是“义”不可能是救世主。义字所文系的这种义文化不是传统社会中所谓的“适宜社会生活的正当行为”的义,而是一种江湖规矩,是一种可以“兼爱”、“尚同”为基本的简易墨家文化范式。这个范式当然只适用于集团内部。
相别与传统社会中儒家倡导的 “有阶级的仁爱”,墨家更强调的是梁山义军最迫切需要的“视人之身若视其身”的思想境界,这种“博爱”正是梁山集团成员急于脱离“良民”加入流氓集团的动机。这种江湖规矩,是流氓群体所认同、推崇、奉行的游戏规则。正是这种规则让仗义疏财、急人之难的宋江成为英雄心目中的“英雄”。
简单的情义伦理并不是一架可以高速、有效运转的社会规范,更不是法律。正统社会里有文护社会秩序的两个支柱,即法律和伦理。各个朝代都倚重这两大支柱,这些规则,伦常也是社会下层人民的依靠:违法必然受到惩处,违理必然受到谴责。一旦这两个支柱倒不再为人民倚靠,再庞大的帝国也会瞬间灰飞烟灭。梁山集团显然不识的这个道理,他们只是用最简单的一种伦理来约束成员,没有创新性的提出一种可以支撑社会运转的架构。孙中山提出了“三民主义”,埋葬了封建王朝,但是梁山集团依然是封建社会的附属物,不可能提出先进的、可以打破常规的理论或者方法。
因而,英雄成员的“非英雄”行为丧失了大部分的民心:滥杀无辜、以杀人取乐、残忍对待妇女及其他的完全没有尊重人权的行为。这种作为让起义的力量没能壮大起来。尽管梁山集团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并不能挽救集团本身的缺憾,最终成员“十去其八”,抱恨收场。
四 结语
梁山集团的滥杀行为遭到人民的坚决反对,没有争取到人民的支持。纵然是水浒集团占尽了天时地利,有如神助,也不能在人民群众的汪洋洪流中前进一步。那种“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想法,自然的也成了空想。集团失败的最根本的是群众基础的及其缺乏,这也是历次农民起义失败得到的血的教训。梁山集团成于义,最终也败于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