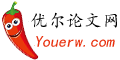
他是一个热爱人类的人,然而处处被人类的阴险毒诈所伤刺了以后,就不得不厌弃人类,厌弃社会了。④
郁达夫对卢梭的这段评论很能说明他自己。表面上,郁达夫确实有些厌弃人生,他觉得“人生的一切都是虚幻”(《过去集•北国的微音》);他把自己的生活称之为“只有眼泪与悲叹”的“残败的历史”(《寒灰集•自序》);他在世上只看见黄灰色;他仿佛“看定了人生的运命”,好像厌倦了生活,甚至载作品中企图自杀,欣赏“自己的死灭,精神的死灭”……然而,所有这一切厌世的表白,绝望的呼喊,恰恰证明了他的“心”并未真“死”!倘若精神真的“死灭”,他还要在文学中愤世嫉俗、自伤自悼做什么呢?早在二十年代就有人指出:郁达夫“表面上似是嫌恶人生而赞美死,其实是酷爱人生而不愿死”,他是“求理想的生活而不得”,才“以死压人”,因而使人“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求生不得的可怜”。⑤
在感情实质上,郁达夫强烈地爱着人生!他有美好的社会理想,他有光明的生活希望,他带着诗一般纯真的感情去想象去触碰人生。是严峻残酷的现实击碎了他的理想和希望,是混浊丑恶的社会嘲弄了他的诗情与天真。的确,在黑暗面前,他无力勇猛搏击,而是深深地陷于伤感的泥沼;但他的内心深处,却依然迷恋着社会,酷爱着生活。“忧郁”与“理想”是郁达夫精神的两个极端,他比正常人更敏锐地感应着世间的罪恶,他又比常人更痛苦地渴求正义和美。他之所以要苛刻地谴责自己“对人类、对社会,甚而至于对自己,有益的事情,一点儿也没有做过”(《寒灰集•自序》)正是因为他确信:即使是个“零余者”,“活在世上,总要做些事情”,⑥不幸的人们可以抱怨社会,甚至诅咒社会,却不能回避对社会的责任。这种为人生尽职的良知与信念,在他身上不仅没有泯灭,而且是经常在驱迫着他,构成了郁达夫艺术生命的内在动力。他不是虚无主义者,他并没有否定生命,更没有否定自我,所以也没有否定一切。他自己正是要竭力肯定生命,突出自我,表现一切。
3.2 郁达夫的“忧郁情结”,消沉是表象,反抗是实质。
正因为他的心并未真正“死灰”,正因为他执著地爱着人生,所以他作品里的忧郁感伤就不仅仅只是忧郁感伤,而是在消沉的表象下隐伏着积极进取的本质因素。郁达夫的一生,始终站在黑暗社会的对立面,他曾表白过自己的立场:
我想以一己的力量,来拼命的攻击这三千年来的恶势力。我想牺牲了我一己的安乐荣利,来大声疾呼这中国民族腐劣的遗传。我想以一枝铁笔来挽回那堕落到再无可堕落的心。⑦
在政论性文章中,他鼓吹革命,正面抨击黑暗;在文学创作里,他愤世嫉俗,倾泻个人哀愁——虽然表现不一,但反抗的实质却是相通的。面对复杂的社会动乱与严重的人性被扭曲的现象,艺术有时也可能以一种不正常的形式(比如追求病态美,夸大丑恶,突出畸形,歌颂荒诞等等)来加以反抗。
郁达夫在《寒灰集•自序》中有这样一段告白:
我是弱者,我是庸奴,我不能拿刀杀贼。我只希望读我此集的诸君,读后能够昂然兴起,或竟读到此处,就将全书丢下,不再将有用的光阴,虚废在读这些无聊的呓语之中,而马上就去挺身作战,杀尽那些比禽兽还相差很远的军队。那我的感谢,比细细玩读我的作品,更要深诚了。
郁达夫如此过甚其辞地贬抑自己的感伤艺术,正说明他希望他的感伤艺术能间接产生某种积极效果。当然,个性主义的感伤情调,可能导致消极的影响。但我们无法否认这一点:颓唐的背后是反抗,“忧郁美”或多或少包含着正义的战斗的力量。正因为如此,郁达夫“把自己的感伤凝结成为诗词文章”,才可能“为时代、为自己作了忠实的记录”;⑧ 才可能在当时的革命青年中成为颇有影响的“极有力的读物”。⑨
4.折射当代社会中的“忧郁”现象
郁达夫的作品在当时拥有大量的青年读者,他使若干青年对生命的意义,自身的问题获得适当的新的认识,但他却不曾指点或暗示一条出路。他强烈的主观色彩与特有的“忧郁”不仅在当时引起巨大的反响,就是在当今社会,我们重视郁达夫的“忧郁情结”带给我们的那份情感上的震撼的同时,更多的应该是关于他这种情感的理性思考。
4.1应当正确看待“忧郁”情绪
科技发展了,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近了,然而心灵却愈来愈远了,人们开始在繁华的城市里感到孤独、苦闷。“忧郁”、“郁闷”在时下仍是比较流行的词汇。人的一生中或多或少都会碰到极大的挫折与压力,或因人际关系、感情因素、家庭因素、经济因素、工作或学业的困扰等诸多压力事件,情绪无法获得有效的缓解,周而复始一再累积,很快就会产生“忧郁”情绪,再加上压力的累积,又缺乏适当的情绪调节与良好的社会支持,会将情绪状态延伸为一种病态,以至于心情与行为都受到影响,于是产生无法脱离的低落情绪,严重者甚至以自杀结束宝贵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