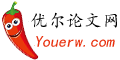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 第5页
索绪尔的宏大构想,是展示一个伟大发现:存在着种种神的名字,诗人以神秘而固定的样式创制出来,编织入(梵文、希腊文、拉丁文)古诗的行节中,这些名称经由依次选择数个特定的字,使其可被人理解。简括地说,索绪尔发现诗是双层的:行上覆行,字上覆字,词上覆词,能指上覆能指。这种变换字序以形成新词的圆转若环的现象,索绪尔以为到处都可见;他被它迷住了;若是听不到原初意义的籁籁细响,他就无法读一行诗。若干字结了盟,播撒遍了诗行,历历在目……意义决不是单一的,数个字形成一个词,虽则每个字理性上都是毫无意义的,字继续在我们身上寻觅它的自由,去意指别的什么。
—摘自罗兰•巴特《文之悦》
二播撒:结构主义与文学
结构主义从语言形式中获取灵感的源泉。表现在文学作品上,结构主义培育出一种新的创作技巧和新的感受性,它甚至宣布包括存在主义小说在内的从前一切小说表述方式的死亡,声称小说陷人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以结构主义为创作手法的新小说变化了语言的表述方式,模糊了文学与文学理论之间的界限,或者小说与非小说之间的界限,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之间的界限;新小说淡化主体或者作者在作品中的统治地位,宣称最重要的是文字本身,是文字在不确定的展开过程中的“互文性”(互释性),或者叫做文本“结构”,或者像是手工编织的不同针法。一个名叫阿蒙(Hamon)的评论家这样说:“询问1960年到1975年的文学概念,就是消解的历史。”①结构主义语言学为文学的冒险提供了理论依据。新小说宣称,文学并不是在其它语言之外的一种特殊语言,文学就是语言本身,在各种语言类型之间并不存在人为的界限。
像结构主义一样,新小说的基本原则也是隔离人的主体性,有意排斥传统小说中人物角色的作用,并且向传统小说中单线条的情节叙事方法提出挑战。以巴尔扎克为典型代表的19世纪小说表明了传统小说总的倾向,即所谓“现实主义”:文字是表达、代表、转述现实生活的,或者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者是通过其它途径获得的间接经验,总之,就像福柯曾经批评过的:文学固执地以为“可说的”可以表达“可见的”,认为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不言而喻的同一性。
新小说批评的始作俑者是萨罗特(N. Sarraute) 1950年发表在《现代》杂志上的文章《怀疑的时代》,作者旨在更新20世纪早期以普鲁斯特和乔伊斯为代表的现代小说写法,不写任何从“我”出发的感受,不是以“我”为中心划一个圈子(这种现代文学手法也被称作“意识流”)。新小说的感受首先在于从外部、在“我思”之外描写。换句话说,新感受去除了在它之前从“我”或者作者出发的两种典型表现,它们与普鲁斯特和乔伊斯有密切关系,其一是时间性或者历史性,表现为记忆或回忆;其二,这种记忆通常陷入“自我”的情感,它在18世纪曾经表现为卢梭式的古典浪漫主义传统,在19和20世纪初期则是所谓的“意识流”小说,或者称作“精神分析”。但是,毕业论文
http://www.Lwfree.cn/在新小说看来,以时间为标志的心理描写是新文学感受的障碍,在这方面新小说与在它之前流行的超现实主义一脉相传,其基本特征遍及绘画、诗歌、音乐等各个文艺门类。值得注意的是,新小说在马拉美和瓦莱里的作品中寻求灵感,这两个作家都强调文字本身的创造作用,瓦莱里曾认为的:所谓文学,不过是对语言特性的应用,是语言自身的延伸和蔓延。
法国最重要的新小说家有米歇尔•布托尔(M. Butor),罗布•格里耶(Robbe Grillet),克洛德一西蒙(Claude一Simon)、勒克莱齐奥(Le Clezio)、杜拉斯等。他们也活跃在((泰勒》杂志周围,与新小说文学理论家交往频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小说家自己往往也是重要的文学评论家,这并非他们刻意而为,而是新小说的文字特性使然,就像新小说的一个前辈纪德在著名的《伪币制造者》中曾做过的那样:书中主角之一、小说家爱德华本想创作一部标题为《伪币制造者》的小说,但是他写的小说其实并不是计划中的小说,而是如何写这本小说—这也是新小说的典型特征,不是跟着作者的想法走,而是跟着文字走。这些文字既是文学评论,也是文学创作。新小说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就在列文一斯特劳斯发表《忧郁的热带》的1955年,罗布•格里耶以他的新小说《旅行者》一书获得当年的评论家奖。两年后布托尔又以小说《变化》获得该奖。1958年,《精神》杂志为新小说开辟了专号。每一个新小说家都有自己的风格,但他们都排斥传统小说的写作模式:他们试图使古典小说样式的人物角色消失,使读者的注意力转向话语内部的关系。新小说认为,所谓“实在”并不是在语言之外,“实在”不过是从语言内部关系所制造出来的效果,“实在”就消失在语言之中。
新小说的这种变化使结构主义的“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不期而遇,这也是西方现代派小说难以读懂的主要原因之一。罗布•格里耶曾经提到福柯在《词与物》中引用多次的阿根廷现代作家博尔赫斯(Borges ),他们共同感兴趣的不是文学描写什么样的题材,而是首先使文学成为一个具有哲学性质的问题。他说:“我越来越相信哲学与文学的对象是一样的。”②他于1963年发表了一本自己自1955年以来的文学评论集《新小说宣言》③,他像《伪币制造者》中的小说家爱德华那样阐述了自己的创作原则:要在小说中排除对人物意向性要素的描述,因为这样的描述似乎使世界只是因为小说中角色的存在而存在,而在新小说中,“那些举止姿态和对象在成为某种事物之前就早已经存在了。”④这里的“存在”不是物而是词。这句话的含义是,物就是词,它们并不需要对人物作所谓深层次的心理描写,并不需要这样的心、理描写所形成的意向对象。所谓的深度描写不过是作者虚构出来的神话,或者换句话说‘,新小说排斥解释和解释学的方法,排斥意指关系中的意义。一种罗兰•巴特一样的零度写作。在新小说这里,就是与看得见的世界或者存在的世界拉开距离,或者说,把它们折叠在小说语言的褶皱中。文字也不再是价值的承担者,因为“价值”从来与时间概念联系一起,比如“永恒”或者“不朽”,“一去不返”等等,但是我们知道,新小说和结构主义一样排斥时间概念,它只守住当下的状态,堵塞记忆的渠道—这样的小说就好像是一种哲学问题的练习,但情景却是文学的,比如这个问题的题目可以是,如果不存在时间上的“过去”,世界将会怎样?人的活动、行为、话语、姿态将脱离人为的系谱或来源,它们会以共时的姿态同时展示在我们面前,使时间上的没有关系变成空间上的有关系,它是没有关系的关系,否定时间上的连续性。
罗兰•巴特对罗布•格里耶的作品《旅行者》大加赞扬,认为这部小说实践了他所希望的“零度写作”,有一种把可见的世界隔离起来的目光。文学家、文学批评家、结构主义者又一次走到一起:他们关注写作现象,写作本身就是一个哲学问题,是语词排列的关系问题,是语言的多样性问题。在这些人中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界限也倾向于消失:理论就是实践,反之亦然。这也是消解或者解构,消解不同叙述类型之间的界限,它们只是文字或词语,如此而已。罗兰•巴特坚持文本之外一无所有的立场,从这里出发他主张所谓“文本的快乐”和字码的多样性。罗布•格里耶则把罗兰•巴特同样的意思说成是镜面上的游戏,所谓“镜面”就是词语的表层,词语一个挨着一个,词语不确定地出现,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而又在意指到它们的含义或者意义之前就被另一个“能指”或者词语所代替,从而抹掉了自己的痕迹。于是在结构主义哲学发生的场所出现了文学,它解构了真实语言与虚构语言之间的界限,或者说,结构主义语言是一种消解被表达对象的语言,一种虚构的语言。
另一个重要的新小说家布托尔的代表作品是《米兰信道》、《管理时间》、《运动》,他使用的一个重要技巧是并列或者同时展示本来属于不同系列的词语和句子,比如把一般句子与引文、报纸段落、广告词之类放置一起,就像是一幅拼贴画毕业论文
http://www.Lwfree.cn/,贴在书页的表面,产生一种类似电影中蒙太奇的效果,出其不意,让人震惊,这是一种“文本的快乐”。罗兰•巴特称赞布托尔这样的文体是新小说继颠覆古典的叙事方式之后,对“书”的观念本身的挑战。同样是对传统阅读方式的挑战:不是读出词的意思,而是看那些词的表述形式;阅读的目光不是一条线性的,不像一条流淌的河,而是在这种线性的展示之外。接不上线,或者说,在叙述的意料之外,把不同的线索接在一处,平列出来。这里出现了另一个术语textualit6,现在通常翻译为“互文性”,像一条不同种类文字共享的地平线。
罗布•格里耶在《新小说宣言》中声称,新小说出现的同时也重新发现了人:即绝不以过去的时态,或者说,以重复的眼光描写人。他认为这样的眼光是荒谬的、有害的。他呼吁:“合上我们的双眼,使我们看不到现在所处世界中的真实情景,重复的叙述只能妨碍我们建立明天的人和世界。”⑤他引用博尔赫斯在《虚构》中说的:20世纪小说家只关心词语,并且为了词语而重写词语。什么样的词语呢?像是喝醉了的、吸过毒的、极度兴奋的、精神分裂的、嗜好神秘性的、不幸的词语;或者叫做背叛形而上学的词语,一些被遗忘、被丢失、或者从来就没有被发现的词语。作为他灵感的源泉,罗布•格里耶提到了卡夫卡的日记、福楼拜的通信集、纪德的《伪币制造者》,以表明20世纪小说于巴尔扎克风格的不同就在于前者是一个虚构的时代,而非表现实在的时代,怎么写而不是写什么成为一个重要问题。罗布•格里耶认为,20世纪小说并不是以某种预先建立好的理论指导未来的文学,恰恰相反,小说不在以任何观念或者意识形态为先导,而是以词语以及词语在不同作家那里特殊的形式(或者风格)为向导,这些形式是多样性的,它们是被发明出来的:这源自对词语本身的热情,它超越自然主义或现实主义、超越形而上学的澹妄。不把文化的任何“条纹”,无论是心理分析的、道德说教的、还是形而上学的因素强加给事物。但事实上,传统小说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强加于事物,我们非常熟悉传统小说中这样的角色、故事情节,没有陌生感,很好理解,而新小说排除这样的“强加”,使我们对它的文字感到陌生,难以理解:因为没有事先设计好了的感情冲突,行为动作失去了精神的指导,如此等等。这些“条纹”也是一些有色眼镜,罗布•格里耶说,不要这些眼镜,不要为文学设置感觉的栏杆,不要把词语当成表达某种立场的工具。
新小说遭遇到具有任何文学创新都将面临的困境,即必须克服原来的阅读和写作习惯。一切习惯都是后天强加的,事物在成为某种习惯所认为的样子之前早就在那里了,它没有意义,既不荒谬也不伟大,在习惯评价它之前和之后都是如此。新小说的这种态度剥夺对事物的解释,去掉意识强加给事物的神秘性。如果用结构主义术语表示,新小说的“能指”不指向任何自身之外的意义,而是转化、交换为另一个“能指”,是拒绝深度。它“走出人类热情的深渊,只是为外表平静无华的世界提供一些信息……在我们看来,事物的外表不再是其内心感情的某种伪装,而是预示着一切超越形而__匕学的因素。”⑥
罗布•格里耶批评了传统小说的主要构成要素:
1.人物或角色必不可少,要有名字、家庭、职业、要有一种“性格”、甚至有一幅反映这样性格的容貌,一种塑造了这种“性格”的经历。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的共J性在于,每一种性格都操纵着具有这种性格的人的行为,换句话说,角色不能有超出自己性格的行为。面对每一个事件,具有一种固定性格的人物会有怎样的行为,是读者可以预料到的。作者可以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 第5页下载如图片无法显示或论文不完整,请联系qq7520187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