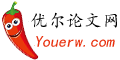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 第6页
让读者爱或恨被制造出来的某种性格。人物的心理行为应该统一,就是说,不可以改变性格,以便于读者判断英雄、无赖、聪明人和傻子。
这样做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不会出现意外,没有震惊或惊喜。罗布•格里耶认为20世纪重要的小说家一般都放弃了这种写法。放弃典型人物和典型性格,甚至放弃人的名字和人物。作为例子,罗布•格里耶提到了剧作家贝克特(比如他的《等待戈多》)和卡夫卡的小说《城堡》。
2.故事:传统小说等于讲一个好听的“故事”,传统小说家应该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要善于制造具有戏剧性的情节。当然,情节要有连贯性,即围绕一个中心线索展开。在这个过程中,“文字从来不会引起疑问,人们只会称赞小说家的表达用词准确,使用了令人愉悦的、有感情色彩的、能唤起丰富联想的方式……文字不过是一种手段……小说的本质,它存在的理由,它的内容,只是简单地讲故事。”⑦
3.内容与形式:传统小说认为内容决定形式,内容就是深度的意指关系,它决定了在同一本书中不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但是,在新小说那里,不是精神去捕捉文字,而是文字占据精神的位置,词语和句子搭起一座建筑,就像一幅由线条和色彩组成的绘画,奥妙在线条和色彩构造的和谐关系,而不在于它与外部世界的某样东西是否相似。同样,新小说文字的神秘性不在于它表现了什么,而是如同象形文字中的书法一样,奥妙在那些变了形状的道涤啪身。形状构成了书法家打动观赏者的主要因素,形式在新小说家那里也构成打动读者的特殊世界。那么,什么是这些形式方面呢?比如改变动词的时态、替换用过去时态叙述的人称代词,破坏深度的理解习惯,比如叙述毕业论文
http://www.Lwfree.cn/的人称不再用“我”而是用“你”;改变词句原有的排列秩序;一个新小说家“什么也不说”,或者他讲究的不是说点什么,而是怎么说的方式,他用方式创造世界。这个方式是他创造出来的,并不是模仿的结果。所以新小说特别强调写作技巧、所谓花招、像变化魔法或游戏。它的态度是“玩”而不是传统的“认真”,忽视理由、根据、动机,从而按照传统小说的眼光,新小说是一种不可能的小说,或后者创造了不可能性。新小说的“建筑”没有宣传和教育这样的使用价值,它让人欣赏但不向人灌输,它的力量在于它没有力量。
新小说抵制悲剧。就像罗兰•巴特所说,悲剧不过是人类专门收集不幸的方式。但我们也可以拒绝这样的方式,寻找使人类快活的方式。悲剧的主角是人,世界成为人的活动,由不同人共同上演的戏剧;但在罗布•格里耶看来,事物是事物,人是人;事物并不人有任何表示,它与人毫无共同之处:这样的倾向显然是“隔离”而不是任何拟人化的升华,舍弃任何理想化的色彩。进一步说,在技巧上,新小说把语言与人的主体性分开,使语言与人的自主意识保持距离。具体说,它只是描写人做了什么、看见什么、下意识地在脑海中浮现出什么,但是不写人想到了什么:对看见的东西没有企图,不设计把它据为己有的诡计—保持事物的陌生感,不对它做任何肯定或者否定的表示,热情和目光都只是停留在事物的表面。罗布•格里耶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在不经意间我们突然对刚才看见的天空感到陌生和诧异,因此我们重新观察,发现天上云彩的形状像一匹马,在接下来的描述中就可能写到云彩在“奔跑”。这样的书写或阅读就是顺着一个所指关系的链条蔓延,在这个过程中谜底始终是不出场的,就是说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传统小说是要求这个标准答案的,因为它总想占有事物。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所谓“标准答案”,总是对“人”有利,因为人与事物的关系是不对等的,人实际上是自问自答,人观察事物,但是事物并不观察人,事物也被剥夺了回答的权利。另一个例子是作为人类劳动工具的锤子,在功利性的意指关系中锤子完全被人化了,就是说,它不是个“东西”,而是一种工具;但是如果放弃人的功利目光,这个东西就不是锤子,它和任何别的东西一样,没有任何用处,这就是新小说家所谓脱离了意义的意指关系,或者称作意指关系的缺失:新小说面临“无”,它不需要破译什么东西。于是,它说另一种语言,不要求回答的语言,没有目的性的语言。
罗布•格里耶认为,加谬小说描写的荒谬性就在于,在人与世界之间、在人的精神灵感和世界不能满足这种灵感之间,有一条无法跨越的深渊,无法超越的鸿沟;荒谬性不在于人或世界本身,而在于人与世界之间只能建立一种陌生的关系,或者说是一种外在的关系。萨特在小说中把这样的关系描写为“恶心”,他让人物的目光非人化,比如在看东西时不是注意它的形状或者线条这些能使人辨认清楚对象的东西,能说出意义的东西,而是被它们的颜色吸引,或者像另一个新小说家勒克莱齐奥在其成名作《诉讼笔录》中的角色亚当那样,不是被女友漂亮的脸蛋和腰条吸引,而是像狗一样喜欢闻雌性的气味。
这些视觉与嗅觉等在与世界发生关系时,便是一种不透明的,陌生的关系。罗布•格里耶还认为,在手法上萨特掏空了词语的惯常意义,就像萨特说的:“黑的?我感到这个词很空洞,⑧它以异乎寻常的速度掏空了自己的意义。黑的?它的词根不是黑的,它也完全不是这树枝的黑……而是说,它搀杂着某种黑的想象,那是绝对看不见的黑,留不住注意力的黑,模棱两可的黑,超越颜色之外的黑。”颜色不再是僵死的,词语可以使它生机勃勃,像是可以触摸到的—但这种感觉说不出来,它一旦说出来就是诗。比如说一种温暖的颜色,像是一股暖流涌人心头—这叫做在颜色中搀假(文学中的术语称为“通感,’),使它脱离原来的所指,与原本不相干的能指搀在一起,但在效果上却使自己活泼异常;但这并不是进人事物的深度,罗布•格里耶说,事物的深度能淹死人,使人丧失对事物敏锐的感受力。深度描写无非是从先验的意识出发写人对事物的感受,但新小说家说,人的眼光并不高于事物,可以用事物眼光看人,或者与事物眼光并列。
罗布•格里耶提到法国现代诗人蓬毕业论文
http://www.Lwfree.cn/热(F. Ponge),后者在作品中几乎不再描写,即回避类似“什么”这样的“所指”问题,这样写的效果就是拒绝深度效应。深度效应在文学上是悲剧效应,即引发人们寻找文字背后的观念;相反,喜剧效果只停留在事物表面。传统文学模式是被深度感情或者思想支配的,甚至19世纪的象征主义也是这样。新小说把自己在读者眼中的晦涩性竟说成是“透明性”,认为在写到的事物之外,没有什么躲藏起来的东西,或被象征的东西,没有背后的思想。但为什么新小说还是难读?这是因为它抛弃了事先的设计,词语的结合违反传统的规则,把似乎不和谐的因素或互相外在的组合在一起,组成隐语一样的意指关系之链。罗布•格里耶称这是空洞的,什么也没隐瞒的神秘。“词,就是不在场”,词和句子就是对象,词语的那些可以利用的“意思”其实没有任何意思。罗布•格里耶还以法国著名剧作家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为例子,说明新小说的立场:除了一棵树便没有或者几乎没有布景,就像什么也不能表示的词语。出场的两个人物,没有年龄和职业,没有家庭背景:这是两个流浪汉,在体貌上也有残缺,他们几乎没有什么话要说,偶尔彼此称呼几乎不像是人的名字,一个叫“勾勾”(gogo),一个叫“低低”(didi ),两人左看看,右看看,做出要离开的样子,却又总是留在舞台上,因为他们没地方可去,不能放弃等待一个叫戈多的人。一个报信的男孩告诉他们:“先生们,戈多今天不来了,但是明天准来”。然后,光线暗了下去,黑夜降临,两个流浪汉决定离开,第二天再回来,但却没有动窝,大幕落了下来。在这之前,还有另外两个角色上来消遣打趣,一个叫波左,他还有一个仆人,叫吕克。波左坐在板凳上吃鸡抽烟,吕克在一旁听差,这就是第一幕。第二幕发生在第二天,但这是第二天吗?是昨天之后还是昨天之前呢?一切布景还和第一幕一样,“低低”在台上唱歌,“勾勾”在吃饭。波左和吕克回到台上,但那个吕克是个哑巴,波左是个瞎子,什么也回忆不起来。第一幕报信的那个小孩又回来了,带来和上次一样的口信:“戈多今天不来了,但是明天准来”。又是同样的夜晚,这两个流浪汉也许因为失望或不知什么原因决定上吊,不幸的是他们没有上吊用的绳子,他们决定走人,第二天再回来,但还是不动窝,大幕落下了。就是这样一出乏味的戏,演了几乎3个小时—这是一段难熬的,几乎没有理由持续的时间,两个主要角色几乎什么也没有做,什么也没有说,他们唯一的表现就是出场,但是这样的出场等于不出场。不在场的戈多就好像是上帝,只要他不出场,舞台上的情形就是那样荒诞;不出场的戈多还是死亡,他明天再不来别人就要上吊;不出场的戈多还是沉默,在等待他的时候人们无话可说,或者人们有权从头到尾保持沉默;戈多是一个达不到的“我”。剧中的两个流浪汉象征着一般的人类,他们固执地等待,就像等待一个观念,一个深层次的意指关系,他们也同样固执地拒绝其他意指关系,这就是人的悲惨境遇,人一生上演的戏剧:人的一生其实什么也没有看见,人们说的和写的全都是废话。
所谓“荒诞”就在于“没有意义”。在“没有意义”的意义上,无论人们喋喋不休的说话或者保持沉默都是荒诞。人们或者保持沉默,或者重复每天都要说的废话,所以这些话的内容或意义是荒谬的。这两个流浪汉通过“戈多明天准来”这样的话语打发掉的时间等于消解了时间,因为时间并没有真的流失,这样的一天和100年是一样的,C' est toutjuste un alibi(这正是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又参见德里达新作Without alibi,也可以译为《没有借口》)。但是,不在现场的时间是必须在现场的,过去和将来都不过是现在。两个流浪汉想离开,但是动弹不得,他们必须在台上等着戈多,从剧的开场直到结束,没有将来和过去,只有现在。人没有选择不在场的自由。但同样荒诞的是,这个在场却是一个“无”,一个没有现实的在场,在观众眼里都等于什么也没有看见,无论人离开还是留在人生的舞台,都预示着死亡。
一个永远的“现在”就等于把时间化作空间,但又是一个死的空间,被剥夺了意义的空间。在这里《等待戈多》与新小说合拍了:那就是没有意指的意义,意指的对象是一个缺失,一个空白。人在空虚中,在黑夜里,没有歇息的场所和目的。不在场,就像索绪尔、勒文纳、拉康、德里达都一致同意的,人不在这里,人总是在别的地方,而别的地方又在别的地方,以至无穷。
1963年,罗布•格里耶在《时间与今天记述中的描述》一文中,阐述了他对新小说的新观点:他把小说与电影的功能做了类比,认为小说的重要欣赏效果不是理解,而是像影像一样让人观赏。他首先指出,文学评论与艺术本身相比更加困难,因为后者只要制造出让人喜欢的效果就行了,而前者却必须指出艺术怎样才能被人喜欢。艺术的困难在于没有俗套,因为俗套本身就难以让人喜欢。为了不落俗套,作品就得有新的意指关系、新的道德,发现一个新的毕业论文
http://www.Lwfree.cn/世界。新小说并非与现代技术无关,它借鉴了电影的手法:制造让人观看的效果,而不是简单地让人阅读。罗布•格里耶认为,新小说是流产了的电影,文字不能像电影那样全景式地展开,只能费劲地一页页翻看。小说能达到电影那样的效果吗?小说也有自己的镜头吗?小说没有镜头,它的词语就是它的镜头。新小说的技巧是放弃了对时间的线性描述,它用片段的空间化了的时间构造自己的平面和建筑。
如果线条就是传统小说讲述的故事情节,那么新小说把各种各样的线条堆积在一起,特别是“剩余”的“念想”;新小说就像狄德罗在一部喜剧性小说((雅克和他的主人》那样,并不需要一个开头,开头可以突如其来,同样的线索可以是开头、中间、结尾,因为还有与它并列的线条。它的效果就是:开头了,但不像是开头,结尾了,但不像是结尾。在有限的篇幅中尽可能多地展开线索或者镜头,也可以称作岔路。电影中的蒙太奇就是走岔路,它把在时间和空间都不在一起的镜头组合在一起。新小说也追求这种蒙太奇式的效果,一种立体性的效果,因为它同时有不同层次的描述。线性流动的时间在这里不再起作用,因为线索不是按照时间顺序安排的。同时出场的东西是被德里达称作“不在现场的证明”的东西(就像《等待戈多》剧中那两个流浪汉),而并不是真实的,现在出场的东西。像电影一样,小说也可以把影像作为探索的手段。影象的可能性也是小说的可能性:电影同时能看也能听,观众在声音中听到了他在画面中看到的东西;如果应用法国新浪潮电影的蒙太奇效果,虽然听和看是同时的,但听与看的内容又可以不一致,就像“文革”期间我们批评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污蔑中国的记录片:在听阿庆嫂唱样板戏时出现了猪吃食的镜头。从结构主义立场看,这里只涉及意指关系的改变,而与在这种关系之外的对象和意义无关。新小说还借鉴了另一种电影效果,就是模糊“真”与“假”的东西,消解现实与幻觉之间的界限,国内读者比较熟悉的昆德拉的作品就是这样。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 第6页下载如图片无法显示或论文不完整,请联系qq7520187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