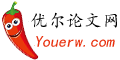
第二,以学术创作对民族之情、知、意进行灌溉和培植。张君劢认为,从民族情感、民族理智的发生进而形成决定民族行为的民族意志,这是情、知、意三者的融合过程,它构成了民族建国的“大前提”。但是这种融合是既“非政府或警察之力所能强致”,也非仅靠一般意义上的国民教育所能实现的。证之以外国历史,英帝国发展之先,以莎士比亚、培根、密尔顿等为先导;法国之由大革命中脱颖而出,以笛卡尔、孟德斯鸠、卢梭等为前驱;德意志在统一之前,文艺上推崇哥德、席勒,哲学上推崇菲希德、黑格尔,还有李斯德之经济学,哥丁大学之自然科学,每每都说明了一个共同的道理,即情、知、意的融合,必须“有全国人所推崇之文艺与学说”为之“灌溉”,为之“培植”。同时,证之以近年来中国思想界的状况,什么君主、民主,大家庭、小家庭,旧道德、新道德,等等,各种主张上下参次,甚至互不相容,也证明欲将其统一,“惟有以本时代之吾国人自创一种哲学上、社会上、政治上之学说以资解决”。因此,张君劢在倡导对大多数国民施行基本教养的同时,力劝知识者们努力于“文艺上、哲学上、科学上之创作”;他并亲著《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一书,一方面作为其从事学术创作之具体实践,同时就此从理论上加以阐发。在他看来,民族建国和民族复兴的基础不能是分和争,应该是合与和。“合与和何由表示?曰理智上感情上意志上之融化”。他坚信“今后吾国哲学界诚有如康德辈之大创作,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界诚有如黑格尔、李斯德、洪蒲尔辈之大创作,文艺界诚有如但丁、歌德辈之大创作,有此种种,则全国思想有所折衷,人民情绪欣欣向荣,国论出于一致”。如此,民族建国之大业即“水到渠成”,民族复兴即可实现。
第三,提高民族的自信心,同时重视对外国经验的借鉴。张君劢认为,世界上没有相同的民族性,民族性总是具有各民族自身的特点。一个民族所以区别于另外一个民族,其原因不外乎此。同时民族性与民族的文化总是不可分割的,不同的文化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性,而不同的民族性又决定了民族文化的不同面貌。从这个意义上讲,一种民族性,就存在于一个民族的文化之中。但是如前所述,民族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民族情爱,而民族情爱不能没有民族自信。那么民族性是否可以说首先就表现于对本民族文化的一种信任或推崇呢?张君劢认为这种说法是可以成立的。他说,欧洲国家尽管语言、风俗、宗教相同,但它们为了表现出自己的民族性特点,仍然总是在文学、哲学等方面力求其异,为此尽量推崇自己民族的文化,推崇自己祖先的丰功伟业;即使一些国家虽其祖先毫无成绩可言,他们为了突出自己的民族性或民族优越性,也仍会想尽方法来表彰其祖先。因为道理很简单,“一国国民晓得他自己文化之优点,晓得他的文化与自己有利益,他自然会相信自己,自然会推崇自己”;而相信和推崇自己的民族文化,自然会有利于民族意识的提高,有利于民族情爱的建立,因而也有利于新的民族性的养成。
提高民族自信心要求重视民族文化,但这很容易走向一个极端,即“自骄自大”,将外来文化拒之门外。另外还有一个极端,即菲薄本民族文化,觉得自己“事事不如人”。这两种现象尤其是前者在近代以来屡见不鲜,而这是不利于自信心的真正提高的。张君劢认为,要改变这些现象,必须克服机械的、单一的思文方式,采取“一方加强自信力,一方尽量容纳外来文化”的方针。一方面,“我们民族要自己认清是世界上最优秀之民族。东亚文化是我们祖先一手造成的,其成绩实有过人之处”。认识到目前国势虽不振,但从过去推定将来,“相信我们民族一定有光明的前途。”同时对于自己过去的文化,也要进行“自我批判”,“应以现代为标准,对于历史上的事迹和人物加以一番选择工作“,通过选择,对“合于此标准者”加以表彰。
综上所述,张君劢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之下,提出了一套颇具特点的救国主张,这一主张的核心可以概括为:通过改造人们的思想观念,养成一切以民族利益为中心的民族意识即新的中华民族性,并以此为基础建设近代民族国家,从而使中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不难看出,这是一种文化救国论。文化救国论并非张君劢的首创,在此之前特别是五四时期就因一些进步文化人的大力提倡而颇为风行。而在张君劢所处的年代,挽救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即进行现实救亡则是摆在人们面前的最紧要的任务。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是五四新文化人,暂时放下思想启蒙的课题而投身于政治救亡的现实运动,也就难以避免了。张君劢从五四时期走过来,他目睹了他的一些同龄人的历史转变,但他不愿意改变自己,他仍然坚持把思想启蒙摆在第一位。当然就张而言,他从一开始就与五四新文化人不尽相同。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人所进行的思想启蒙重点是呼唤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是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而张君劢所高举的是民族主义的旗帜,所呼唤的是以民族为本位的集体性民族意识的诞生。张君劢身上所体现的这些特点,一方面说明他对思想启蒙重要性之认识的少有执着,同时也反映出他并不打算把自己封闭起来,而是尽可能地使自己的主张与现实需要求得一致。但是尽管如此,张所从事的仍然是一种远离社会现实的文化救国工作,这种工作虽然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还是无法适应中国社会特定政治形势的需要。而一种工作一旦远离了社会需要,其影响也就十分有限了。
三
30年代,当日本帝国主义者不断入侵、民族危机空前加重的严峻时刻,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及爱国人士不约而同地逐渐将视线转向了民族问题。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思考应对时局之策,形成了各自的民族主义主张,其中最具影响者当数国、共两党。就国民党而言,出于对其执政党地位的考虑以及不可推卸的责任,它明确打出了“攘外”的旗号,只是“攘外”须以“安内”为前提。是为官方的民族主义。共产党是中国普罗大众的杰出代表,为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它主动提出变党派对立为党派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在共产党的旗帜上,不仅写着民族的独立,还写着人民的解放,这使它的民族主义同新民主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与官方民族主义判然有别。除此而外,在为数不少的中间党派当中,以张君劢为首的国家社会党,算是在民族问题上发声比较响亮的了。张的民族主义如前所述具有注重文化的特点,但在国共两党之间它却无法因此保持自己的独立品性,因为它克服不了“民族”、“国家”、“阶级”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些拦在面前的理论障碍。在这些障碍面前,张的文化民族主义只好向官方的政治民族主义让步。
先看张如何认识“阶级”及其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本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同时,不同的阶级又往往属于同一个民族,共同的民族属性可以使其成员具有共同的民族情感,当民族出现危难之时,这种民族情感可以转化成用以保卫民族利益的巨大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但是民族问题并不能完全取消阶级问题,出于不同的世界观和政治立场,不同的阶级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常常出现重大差别。可见只要阶级存在,阶级与民族之间的矛盾也就会存在,阶级问题不会因为民族问题突出而消失。然而张君劢却无法理解二者之间的这样一种辩证关系,他只愿接受民族的观点而不愿接受阶级的观点。因此他反复陈述民族观念强于阶级观念的道理,强调“民族观念是人类中最强的,阶级观念决不能与之相抗。无论是已往的历史,抑是目前的事象,凡民族利害一达到高度无不立刻冲破了阶级的界限”。同时他把“阶级说”说成是一种“以恨为出发点”的“恨的哲学”,认为在这种哲学支配下,整个社会“决得不着和协与平安”。为此他要求人们“必须以全力排斥这个恨的哲学。
再看张如何看待“国家”及其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张氏将“民族”归结于“国家”,又将“国家”的本质归结为“善”,其目的无非是要将“阶级”从“国家”中清除出去。因为阶级所体现的据说不是“善”,而是“恶”;不是“爱”,而是“恨”;不是“总意”,而是“私利”。而在“民族国家”中,只有“民族观念”、“民族意识”才是最高的“善”,才是最大的“爱”,才是真正的“总意”。基于此,张将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马克思主义。他坚决反对把阶级、阶级斗争引入“国家”范畴,完全将二者对立起来,于是很自然的对从事阶级斗争、致力于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共产党产生反感。他认为,共产党主张“阶级论”是“改建新国运动中之大不幸”,中国民族建国至今未获成功,共产党应负相当的责任。因为,“以中国社会构造之脆弱,农工未经教育未经训练,驱之使战,是徒为揭竿斩木之陈胜胡(吴)广而已”,不可能给国家带来任何好的结果。当然站在“公器”的国家立场,张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也曾表示过不满,批评其但知一党之私利而违背了“改建近世国之义”。他写道:“所以教育人民,有数千年之文化的遗产,奚必以党义为至宝;所以防止内乱者,有共通之刑法在,奚必另定反革命之条例;政府当局所为,诚有以餍人民之望,人民自不乐于批评与反对,何必以满布法网为长策。善恶者国家法网之第一标准也,今更以党不党之原则乱之,而欲国民心目中有真正之国家观念难也”。但是尽管如此,他并不愿从根本上否定国民党所代表的“国家”,并不主张对现有国家实行“再造”,而只主张“改建”,或者“改善”。并且,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他代表国社党与蒋、汪互换函件,表示愿率党人“才啭诚团结共赴国难之旨”,“对于国民政府——致拥护”。同时又致信毛泽东,劝共产党将军队、边区全部统一于国民政府,并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
一般说来,民族与国家是紧密相联的;历史的事实也表明,民族主义的最后落实往往表现在民族国家的建立上。但是,国家总是阶级的国家,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国家,国家不是抽象的“公器”。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如果说有“民族国家”的话,那也应该就是人民的国家。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建立“民族国家”的前提就是将现存的由少数特权阶级统治的国家彻底抛弃。张君劢把建立民族国家作为中华民族复兴的现实指标,反映了民族主义的一般要求,这是必要的;然而他对现存国家却采取了最大限度的容忍态度,要求人们无条件地去服从,以为只有如此才能实现民族主义的目标。这实际上是将民族主义的实现寄托在现存的国家身上,是在民族主义名义下提倡对现存国家的忠诚,是将民族主义等同于国家主义。这反映出张氏民族主义在文化和政治的不同层面存在着矛盾,也表明其在政治上已向国家主义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