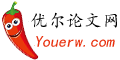
大晏词的欣赏
谈到文学的欣赏,原是颇为主观的一件事。譬如口舌之于五味,滋味既异,嗜好亦别,强人同己,固属无谓的多事,然而美芹献曝,略述个人品味之所得,或者也尚不失推己的一份诚意。因此,我想略谈一谈关于大晏词的欣赏。
在北宋初年的词坛上,晏殊、晏几道父子和欧阳修是并称的三位作者。而一般读者对这三位作者的爱好,则以小晏为最,欧阳次之,而爱好大晏者则最少。大晏之所以不易得人欣赏的原因,我以为有两点:其一是因为大晏词的风格过于圆融平静,没有激情,也没有烈响,既不能以色泽使人眩迷,又不能以气势使人震慑,正如其词集名《珠玉》二字,只是一奁温润的珠玉,虽然澄明纯净秀杰晶莹,然而自有些人看来,却会觉得它远不及一些光怪陆离,五色缤纷的琼瑰更足以使人目迷心动,这是大晏词之不易得人欣赏的第一个原因;至于另一个原因,则是由于大晏的富贵显达的身世,在一般人心目中,似乎都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一种“穷而后工”的观念,而大晏在这方面却不能满足一般人对诗人之“穷”的预期,和对诗人之“穷”寄以同情的快感,这是大晏词之不易得人欣赏的第二个原因。宛敏灏君在《二晏及其词》一书中对大晏的一些词作甚至讥之为“富贵得意之余”的“无病呻吟”。宛君于二晏之身世、作品,搜罗考订极详,对小晏亦赞扬备至,而独于大晏的一些词作不能欣赏,因而颇有微词。昔蒋弱优之评杜甫《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万里戎王子”一首云:“见遗于无意搜罗之人不足怪,遗于搜罗已尽之人为可恨耳。” ①看到宛君“无病呻吟”的话,我真不得不为大晏仕途之幸而叹息其不幸了。
我以为想要欣赏大晏的词,第一该先认识的就是大晏乃是一个理性的诗人,他的圆融平静的风格与他的富贵显达的身世,正是一位理性的诗人的同株异干的两种成就。诗人的穷与达,原来并没有什么“文章憎命达”、“才命两相妨”的必然性,而大半乃是决定于诗人所禀赋的不同的性格。一般说来,诗人的性格约可大别分为两种:一种是属于成功的类型;而另一种则是属于失败的类型。属于成功的一型,就性格而言,可以目之为理性的诗人;而属于失败的一型,则可目之为纯情的诗人。《人间词话》之评李后主词云:“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又说:“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这些话,就纯情的诗人而言,是不错的。因为纯情的诗人,其感情往往如流水之一泻千里,对一切事物,他们都但以 “纯情”去感受,无反省,无节制,无考虑,无计较。“赤子之心”,对此种诗人而言,岂止是“不失”而已,在现实的成败利害的生活中,他们简直就是个未成熟的“赤子”。此一类型之诗人,李后主自是一位最好的代表。而破国亡家,也正为此一类型之诗人的典型的下场。“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对此一类型的诗人而言,其“百凶”之遭遇与其“纯情”之作风,也正为同株异干的两种必然之结果。至于理性的诗人则不然,他们的感情不似流水,而却似一面平湖,虽然受风时亦复縠绉千叠,投石下亦复盘涡百转,然而却无论如何总也不能使之失去其含敛静止、盈盈脉脉的一份风度。对一切事物,他们都有着思考和明辨,也有着反省和节制。他们已养成了成年人的权衡与操持,然而却仍保有着一颗真情锐感的诗心。此一类型之诗人,自以晏殊为代表。《宋史·晏殊传》记载云:“仁宗即位,章献明肃太后奉遗诏权听政。宰相丁谓、枢密使曹利用,各欲独见奏事,无敢决其议者。殊建言:‘群臣奏事太后者,垂帘听之,皆毋得见。’议遂定。”又载元昊寇边时, “陕西方用兵,殊请罢内臣监兵,不以阵图授诸将,使得应敌为攻守;及募弓箭手教之,以备战斗。又请出宫中长物助边费,凡他司之领财利者,悉罢还度支。”从这些事,我们都可以看出晏殊的明决的理性。他的识见与谋虑,都可说得上是将相之才,而决不是一个“长于妇人之手”,未经阅世的“赤子”。然而自其《珠玉词》来看,晏殊又确实是一个资质极高的诗人,由此可知事功方面的成就原无害于一个理性的诗人之为真正的诗人,而《珠玉》一集的价值,也决不该因其富贵显达的身世而稍有减损。我将“理性”二字加诸于“诗人”之上也许会有人颇不谓然,因为诗歌原该是缘情之作,而情感与理性则又似乎有着厘然迥异的差别。这就一般人而言,也许是对的,因为一般人的理性乃但出于一己头脑之思索,但用于人我利害之辨别,此种理性之为狭隘与坚硬,而与感情之格格不能相容,自是显然而且必然的事。然而诗人之理性则有不同于此者,诗人之理性该只是对情感加以节制,和使情感净化升华的一种操持的力量,此种理性不得之于头脑之思索索而得之于对人生之体验与休养。它与情感不但并非相敌对立,而且完全浸润于情感之中,譬若水乳之交融,沆瀣之一气,其发之于心亦原无此彼之异与后先之别。是理性既可以与情感相成而非尽相反,则诗歌虽为缘情之作,而诗人则固可以有理性之详人了。
做为一个理性的诗人,我以为大晏的词有着几点特色。而第一点该提出来说明的,则是大晏《珠玉词》中所表现的一种情中有思的意境。如前所述,理性既可以与情感如水乳之交融,则《珠玉词》的情中有思的意境,便正为此种交融了的理性与情感的同时涌现。在一般人的诗作与词作中虽然也不乏表现思致的作品,但大晏与他们不同的,则是一般人所表现的思致多出于有心,而大晏则完全出于无意,譬如酌水于海,其味自咸,这和有心要泡一杯盐水的人,自然有着显著的差异。如大晏最有名的一首《浣溪沙》词之“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这三句词从表面看来,所抒写的只不过是“伤春”、“念远”的情感,丝毫也看不出有什么思致在其间,而大晏也确实未尝有心于表现什么思致,只是读这三句词的人,却自然可以感受到,它所给予读者的,除去情感上的感动外,另外还有着一种足以触发人思致的启迪,这种启迪和触发,便正是大晏的情中有思的特色之所在。即以这三句词而言,如“满目”一句,除“念远”之情外,它更使读者想到人生对一切不可获得的事物的向往之无益;“落花”一句,除“伤春”之情外,则更使人想到人生对一切不可挽回的事物的伤感之徒劳;至于“不如怜取眼前人”一句,它所使人想到的也不仅是“眼前”的一个“人”而已,而是所该珍惜把握的现在的一切。大晏在另一首《玉楼春》词中也曾有句云:“不如怜取眼前人,免使劳魂兼役梦。”由此一句之重复使用,我们更可以体认出来,大晏之所屡次提到的“眼前人”,实在只是表现了大晏的一种明决的面对现实的理性。这种种联想与体认,在读者亦并不需深思苦想而后得,而是当读者感受词句中的一份情感之时,便已同时感受到其中的一份思致了。那便因为如前文所言,这一份思致乃是由大晏对人生感受体验而得,而并非由头脑思索而得,它原即在情感之中,而并非在情感之外,所以其表现于词亦全属无心,而决非有意,因之这一份思致也就只宜于吟味和感受,而并不宜于辨察和说明。如我之所解释,自不免有牵藤附葛、坠坑落堑之嫌,不过,大晏词之易于引起读者一些有关人生的哲想,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王国文先生在《人间词话》中,对大晏的《蝶恋花》词之“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三句,便也曾经既许之为诗人“忧生”之词,复喻之为“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之“第一境”,这两段话,本文不暇详说,我不过引来证明以哲想解说大晏词并非自我作古。而其所以易于使读者生此种联想的缘故,便正因为大晏的词有着一种情中有思的特色。这种特色,加深也加广了大晏词的意境。如果以大晏与他的儿子小山相较,那么像小山的一些名句,如“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临江仙》),“今宵剩把银钍照,犹恐相逢是梦中”及“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鹧鸪天》)诸句,虽然其“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黄庭坚《小山集序》)之处,大晏自有所不及,然而如只就情中有思这一点而言,则小山词之意境,实在远较乃父为狭隘而浅薄。其原因便在于小晏所表现的悲欢今昔之感与歌酒狎邪之词,乃但为人生之一面,而其所触动者亦但为读者之感情而已;至于大晏,则其所触动者已不仅为读者之感情,而且更触动了读者有关整个人生的一种哲想,因此,大晏词乃超越了其表面所写的人生之一面,而更暗示着人生之整体。宛敏灏君在《二晏及其词》一书中,曾举大晏《憾庭秋》词之“念兰堂红烛,心长焰短,向人垂泪”三句,与小晏《破阵子》词之“绛蜡等闲陪泪”及《蝶恋花》词之“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三句相比较,以为 “向”字尚不及“陪”字之深,更不敢望“替”字矣。殊不知小晏之“陪”字、“替”字虽佳,然而其“陪”人、“替”人垂泪者,仍不过只是一支蜡烛而已,而大晏之“心长焰短,向人垂泪”二句,则使读者所感受的实在已不复仅是一支蜡烛,而同时联想到的还有心余力绌的整个的人生。虽然这在大晏也许未尝有此意,而其特色却正在使读者能生此想。故就情感言,小晏自较大晏为铱挚,然而如就思致言,则小晏实不及大晏之深广,而此种差别也正是理性的诗人与纯情的诗人的主要区别之所在。大抵纯情的诗人,对于人生只有人乎其内的真切的感受;而理性的诗人,则除感受外,更有着一份出乎其外的證明的观照。唯其为“人”,故所失在狭;唯其能“出”,故所长在广。唯其但得之于“感受”,故其所表现者,有情而乏思,而其意境亦较浅薄;唯其能得之于“观照”,故其所表现者,情中乃更复有思,而其意境亦较深刻。除以上所举各例证外,他如大晏另一首《浣溪沙》词之“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喜迁莺》词之“花不尽,柳无穷,应与我情同”,《少年游》词之“莫将琼萼等闲分,留赠意中人”诸作,或者表现了圆融的观照,或者表现了理性的操持。这种特色,正为大晏之所独具。欣赏大晏词,如果不能从他的情中有思的意境着眼,那真将有如入宝山空手回的遗憾了。
至于大晏词的第二点特色,我以为则该说是他所特有的一份闲雅的情调。《汉书·司马相如传》云:“相如时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大晏的闲雅,就正有着这一份雍容富贵的风度。而这一份风度,在我国诗人的作品中,是极为罕见的。其所以罕见的缘故,当然是因为一般诗人们都未尝有过如大晏的显达的身世,因之也未曾有过如大晏的雍容闲适的生活,而有大晏之身世与生活者,则又未必有如大晏的诗人的资质。这种美具难并的机会既不多,因此大晏的闲雅的风格,乃成了他所独有的一种特美。大晏生当北宋真、仁两朝的太平盛世,自14岁以神童应试擢秘书省正字,仕至宰相,其显达之身世,已具见史传的记载,本文对此不拟再加详述;至于大晏的诗人的资质,则可从他的词作中所表现的锐感与善感得到证明。如其《破阵子》词写少女神情之“疑怪昨宵春梦好,元是今朝斗草赢,笑从双脸生”,及《菩萨蛮》词写黄葵之“高梧叶下秋光晚,珍丛化出黄金盏”,“擎作女真冠,试伊娇面看”,这些词句都具有极鲜明的意象,也给予读者极强力的感染,这是唯有一个锐感的诗人才能具有、才能给予的。又如其《玉楼春》词之“陇头呜咽水声繁,叶上间关莺语近”,《踏莎行》词之“春风不解禁杨花,濛濛乱扑行人面”诸句,则凡耳目所及,写得万物都若有情,这更是唯有一个善感的诗人才能感受、才能抒写的。以这种锐感、善感的资质,无论其所遭之境遇之为穷为达,都无疑地该不失为一个真正的诗人,只是因境遇之影响而形成的风格或者不免将要有所不同而已。大晏的境遇是富贵显达的,因之怀着“穷而后工”的成见,想要在大晏的词中寻找孤臣孽子,落魄江湖的深悲幽怨的人,当然不免要感到失望。但大晏的诗人的资质,却毫不曾因此而减损。他的闲雅的风格,就正是他的显达的身世与他的诗人的资质所相浑融、相调剂而结成的佳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