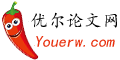
古代诗学的隔与不隔
在《人间词话》中,王国文提出了三组重要诗学范畴:“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宏壮与优美”、“隔与不隔”。其中“隔与不隔”是王国文重要的诗学本文源自优文论文网批评话语。“隔”者,诗词写情、写景之病,表价值否定;“不隔”者,诗词“妙处”所在,表价值肯定。就词来说,它们还是对词史的价值判断:五代、北宋词为“不隔”,南宋以后词则多“隔”;而南宋词即便有“不隔”处,较之五代、北宋词又“自有浅深厚薄之别”。我们大致可以说,“隔”与“不隔”概念体现了王国文对中国古代诗词的价值判断。
然而,细加考量,王国文“隔与不隔”却存有这样的问题:其一,何谓“隔”与“不隔”?其诗学内涵是什么?他并未给出一个明确界定,他只是说“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如雾里看花”便是隔,而如何是“语语都在目前”、“雾里看花”并未说明。其二,更为重要的是,王国文的核心命题是“境界”说,为此提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那么“隔与不隔”与“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之间有无关系?对此,《人间词话》未置是否。王国文以观物方式的不同来区分“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两种境界分别对应“宏壮”与“优美”两种美感形态。他说:“苟有一物焉,吾人无利害之关系,而吾人之观之也,不观其关系,而但观其物;或吾人之心中,无丝毫生活之欲存,而观其物也,不视为与我有关系之物,而但视为外物,则今之所观者非惜之所观者也。此时吾心宁静之状态,名之曰优美之情,而谓此物曰优美。若此物大不利于吾人,而吾人生活之意志为之破裂,因而意志遁去,而知力得为独立之作用,以深观其物,吾人谓此物曰壮美,而谓其感情曰壮美之情。”①又言:“今有一物,令人忘利害之关系,而玩之而不厌者,谓之曰优美之感情。若其物直接不利于吾人之意志,而意志为之破裂,唯由知识冥想其理念者,谓之曰壮美之感情。”②同是我与物,前一种观物,物我之间悠游相融;后一种观物,物之于我极为不适,我之意志破裂。意志原是叔本华哲学的核心概念,它类似生命本能,王国文称之为“生活之欲”。两种观物,本是暂时忘欲、去欲,摆脱人生苦痛的方式,但前者是物我相融、“吾心宁静之状态”;后者则是物我对峙,物迫于我、我抗于物,人纯粹理性地观照物之形式。前者正似物我“不隔”,后者似物我相“隔”。如若这样,则“隔与不隔”与“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宏壮与优美”之间,便可达成桴鼓相应的三组范畴,但王国文并未论及于此。在他那里,“不隔”似与“境界”相关,这从其所举诗例中隐约可见:“不隔”诗例中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无我之境”诗例中也有此例,这似乎表明“不隔”者为“无我之境”;但对“不隔”例举中,除诗外还有词,而在“无我之境”的例举中,却只有诗而无词,这似乎又表明,“不隔”者并不见得就是“无我之境”,后者也并不见得就是前者。
朱光潜曾说,在20世纪前期,他所读过的中国学者关于文学批评的著作,“以王静安先生的《人间词话》为最精到”,而他首先注意到的就是“隔与不隔”:“他所说的诗词中‘隔’与‘不隔’的分别是从前人所未道破的。”③但同时又言:“他只是指出一个前人所未道破的分别,却没有详细说明理由。”“王氏论隔与不隔的分别,说隔如‘雾里看花’,不隔为‘语语都在目前’,似有可商酌处。”④这意味着朱光潜既充分体认到王国文“隔与不隔”说潜在的诗学价值,也表明他要从王国文那里“接着讲”。
朱光潜《诗论》第二章讨论诗境的分别,就是从“隔与不隔”谈开的,不过,他一开始就将其纳入了自我诗学语境:“依我们看,隔与不隔的分别就从情趣和意象的关系上见出。情趣与意象相熨帖,使人见到意象,便感到情趣,便是不隔;意象模糊零乱或空洞,情趣浅薄或粗疏,不能在读者心中现出明了深刻的境界,便是隔。”⑤这有三层意思:一、诗的境界是情趣与意象的契合无间。 二、诗境既是作者创造的境界,也是读者“见”到的境界,它是读者与作品的契合无间。三、情趣与意象合,则是不隔,则有境界;情趣与意象离,则是隔,则无境界或境界浅。朱光潜对“隔”与“不隔”作了明晰界定,并予以科学分析。不过接着他就提出了质疑:“王氏的‘语语都在目前’的标准太偏重‘显’。”而“象征派则以过于明显为忌,他们的诗有时正如王氏所谓‘雾里看花’,迷离恍惚,如瓦格纳的音乐。”⑥“不隔”诗有可能太过于“显”,不见得是好诗;“隔”诗也可能像瓦格纳的音乐,是好诗。…显’易流于粗浅,‘隐’易流于晦涩。”“但是‘显’也有不粗浅的,‘隐’也有不晦涩的。”而且对“显”与“隐”的要求,也因人的生理和心理方面的不同而各异:“有人接受诗偏重视觉器官,一切要能用眼睛看得见,所以要求诗须‘显’,须如造型艺术。也有人接受诗偏重听觉与筋肉感觉,最易受音乐节奏的感动,所以要求诗须‘隐’,须如音乐,才富于暗示性。”⑦我们大致可以得到朱光潜这样的观点:王国文的“隔与不隔”,如果说是用来说明情趣与意象的离与合,并以此来判定诗的优劣,则是恰当的,但如果用来意指诗的“隐”与“显”,并以此来判定诗的优劣,则是不恰当的。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注意到,朱光潜是在王国文“隔与不隔”的基础上引出了“显与隐”的诗学范畴。他说:“诗中原本有‘显’与‘隐’的分别。”⑧“显则轮廓分明,隐则含蓄深永,功用原来不同。”“写景诗宜于显”,写情诗则“宜于隐”,“写景不宜隐,隐易流于晦;写情不宜显,显易流于浅”。⑨所谓显与隐,既是指诗歌写情写景的性质,更指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艺术经验;它们所导致的不同审美功能,反过来又规定了写景宜显、写情宜隐的艺术经验。但显与隐也可能是一种不成功的艺术经验,即“‘显’易流粗浅,‘隐’易流于晦涩”,而这又导致了显与隐作为两种不同审美功能的可能性变异。显然,朱光潜的“显”与“隐”有异于王国文的“隔”与“不隔”,后者是相互对立的价值概念,前者不是:“显”者既可能“轮廓分明”,也可能“易流于粗浅”,“隐”者既可能“含蓄深永”,也可能“易流于晦涩”,各有其好,亦各有其不好。
朱光潜从“隔”与“不隔”拓出“显”与“隐”,目的还不仅于此。“懂得诗的‘显’与‘隐’的分别,我们就可以懂得王静安先生所看出来的另一个分别,这就是‘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分别”,⑩这意味着他要由“显”与“隐”而论及诗境,而前者是后者的前提。不过,他的诗境论同样是从颠覆王国文“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而起的。朱光潜以西方美学的移情说质疑王国文概念的不准确:“他所谓‘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就是‘移情作用’,‘泪眼问花花不语’一例可证。移情作用是凝神注视,物我两忘的结果,叔本华所谓‘消失自我’。所以王国文所谓‘有我之境’其实是‘无我之境’(即忘我之境)。他的‘无我之境’的实例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都是诗人在冷静中所回味出来的妙境(所谓‘于静中得之’),没有经过移情作用,所以实是‘有我之境’。”由此,他提出“同物之境”和“超物之境”以取代王国文“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⑾在他看来,同物之境即是有移情作用,由移情而物我为一;超物之境则不关涉于此,纯由诗人妙悟所得;前者消失了物我,后者不关涉物我而只有我。但是,我们应搞明白在诗学逻辑上,“同物之境与超物之境”与“显与隐”是何关系,因为这关系到以“显与隐”去颠覆“隔与不隔”,是否有意义。朱光潜说: 我以为“超物之境”所以高于“同物之境”者,就由于“超物之境”隐而深,“同物之境”显而浅。又说: “同物之境”和“超物之境”各有胜境,不易以一概论优劣。“超物之境”与“同物之境”亦各有深浅雅俗……两种不同的境界都可以有天机,也都可以有人巧。⑿
从前一段话看,朱光潜有意在“显与隐”与“同物之境与超物之境”之间建起逻辑对应关系:同物之境则显,超物之境则隐。但比较前后两段话,不难看出一个自我矛盾,在前他认为超物之境高于同物之境,前者天机偶成,后者人巧所工;在后则消除了这种价值甄别,以为两种境界不分优劣,都可有天机,也都可有人巧。何以如此?显然他意识到,如果把显与隐作为价值对立的概念,则它们与同物之境和超物之境之间便难以建起对应关系,“显而浅”为劣,本就无所谓有境界,又何能说它是同物之境?这便与王国文的“隔”与“不隔”无法同“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建起逻辑对应关系一样。可是如若消除了“显”与“隐”的价值甄别性就大不一样,显与同物之境之间、隐与超物之境之间便可顺利会通:显与隐作为两种具有原质性的艺术经验,具有两种原型性的审美功效,它们实现为两种审美境界,即同物之境和超物之境;并由此可推而广之去审视文学艺术史的各种现象。
朱光潜注意到文学史的一个普遍现象:越是古代诗歌,同物之境少,超物之境多;到后来,则反过来,同物之境多,超物之境少。在欧洲,19世纪前,诗多超物之境,之后多同物之境;中国诗在魏晋以前多超物之境,魏晋后则多同物之境。朱光潜分析原因说:“‘同物之境’在古代所以不多见者,主要原因在古人不很注意自然本身,自然只是作为‘比’、‘兴’用的,不是值得单独描绘的。‘同物之境’是和歌咏自然的诗一齐起来的。”⒀朱光潜认为中国诗从魏晋前到魏晋后“是由‘自然艺术’转变到‘人为艺术’”,⒁是由“超物之境”向“同物之境”的转移,当然也就是由“隐”向“显”的转移。我们看到,当朱光潜以“隐”与“显”、“超物之境”与“同物之境”、“自然艺术”与“人为艺术”去范畴中国诗史时,其中隐约有王国文的影子,王国文就是以“隔”与“不隔”来考量中国词史的:唐五代、北宋词多“不隔”,南宋以后词则多“隔”。
现在我们可以有这样三个基本结论:(一)朱光潜诗境论是从王国文诗学“接着讲”的,引其发端的就是王国文的“隔与不隔”说。(二)朱光潜以“显与隐”颠覆了王国文的“隔与不隔”,继而以“同物之境与超物之境”颠覆“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建起了“隐”与“显”、“超物之境”与“同物之境”、“自然艺术”与“人为艺术”三者之间的诗学逻辑,毕业论文http://www.youerw.com/使三者成为桴鼓相应的平行范畴。(三)朱光潜以这三个范畴,既来说明诗的艺术经验、审美境界,也来说明中国诗史。而这些都是以变王国文“隔与不隔”的价值甄别为“显与隐”的非价值甄别,有意弥合王国文“隔与不隔”与“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之间的逻辑断裂为前提的。
朱光潜深刻体认到王国文“隔与不隔”说潜在的诗学价值,在其基础上拓开自我诗学语境,这是其诗学理路;他不满于“隔”与“不隔”在王国文那里仅仅作为价值判断的概念存在,从而荡涤其诗学狭隘性,使其成为一组平行性的诗学范畴。总之,朱光潜的“接着讲”是颠覆式的,他旨在建起“显与隐”与“同物之境与超物之境”以至与“人为艺术与自然艺术”之间的诗学逻辑,构成自我的诗境论和诗史论基本内涵。
①王国文《红楼梦评论》,《静庵文集》第68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②王国文《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静庵文集》第54页。
③⑧⑩朱光潜《诗的隐与显——关于王静安的<人间词话)的几点意见》,《朱光潜全集》第三卷第355、356、358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④⑤⑥朱光潜《诗论》,《朱光潜全集》第三卷第57页。
⑦⑨朱光潜《诗论》,《朱光潜全集》第三卷第58页。
⑾⑿⒀⒁朱光潜《诗论》,《朱光潜全集》第三卷第59—60、61、58—62、1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