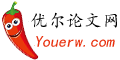在人性真空的世界中挣扎
摘要:俄罗斯作家扎米亚京在长篇小说《我们》中虚构了一个未来时空中绝对理性化、数字化、机械化的“联众国”,以及生活在其中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作家以具有前瞻性的深邃眼光预见到高度理性文明将带给人的精神灾难,以及人所处的理性的环境与感性的内心世界的背反,表现了极端理性主义与人性的悖论。
关键词:《我们》、理性、人性
俄罗斯作家扎米亚京于1920年完成的小说《我们》被视为反乌托邦小说的鼻祖。小说一度在苏俄被视为禁书,作家自身也受到政府当局的封杀。但小说绝不仅仅是将政治话语中的专制集权主义作为矛头的指向,更是对整个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中一切反人性、反自由的强权的批判,预见极端理性必将给个体带来被异化的精神灾难。
个体自我的丧失。联众国中的公民没有名字,除了至高的“无所不能者”外,每个人都是字母和数字组成的号码。所有人都穿着一样的衣服,迈着一样的步伐,按照同样的时间表生活,甚至性生活也要通过上交理性的“粉红票”才能实现。他们住在透明玻璃搭建的房子里,所有房间的布置都一样,彼此透明可见。在这样高度一致化的群体中,公民之间实现了完全意义上的“平等”,“我们”就是“我”,“我”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没有个体的差异,“时间表”是“我们”信奉的《圣经》。“我们”都是“优轮的钢铁巨人”[1],每天早晨同一时刻醒来;同一时刻“像一个人一样开始工作” [1];像一个人一样结束工作;同一秒钟将“汤匙”送到嘴边;同一秒钟出门散步;同一时刻上床睡觉。在联众国的世界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整齐划一的,“最最睿智”的“我们”正是视这种绝对的步调一致为最和谐的节奏。
《我们》中体现的个体自我性的丧失让我们看到了人机械化的恐怖恶果。二十世纪,人类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深重灾难,其本质归根结底是对人性和自由的剥夺,在这一点上,扎米亚京突破了时代的局限,用文学实现了前瞻性的预见,只是我们并没能将这一恶果避免。
http://www.youerw.com 自由与幸福的悖论。联众国的本质在于对人性的最大限度的剥夺或者说是赐予一种“虚假的自由”[1],然而,这种剥夺和虚假正是为了实现联众国公民的“幸福”。小说中D-503看见车床自动运转,感受到如舞蹈般的美妙,“这场舞蹈缘何如此美妙?答案:因为这乃是一种不自由的行动。这场舞蹈的深刻意义在于它对理想的非自由状态毫无保留、心醉神迷的臣服” [1]。联众国中“无所不能者,死刑机,立方体,巨大的气钟罩,安全卫士——这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一切都是壮观、美丽、尊贵、高尚、透彻、纯净的,因为这一切保证着我们的非自由,也就是我们的幸福” [1]联众国中没有自由可言,那些不可思议的行为规范在延续了漫长的时间后已经成为一种惯性的力量,而不再是“规范”的强制性,因此,生活在这样的“乐园”中的人已经陷入不自觉的状态。
对自由的向往是人生而具有的本质属性,无论在禁锢中实现了怎样的幸福,那都是一种“被强制赐予的”、虚假的幸福,甚至因为失去自由的状态,我们根本无法确定那是否能够称得上是“幸福”。自由与幸福的悖论恰恰在于其在一定程度上相互矛盾,却又无法分离。
极端理性的异化。《我们》中的联众国是一个高度理性化的社会,每个人都过着“数学式的完美生活” [1],“我们”的生活如正方形一样稳固、牢靠。“我”的大脑是“像毫无瑕疵的计时记一样完美的机制” [1],从来不会做梦,“我”极度痛恨象征着无理性的-1的平方根,不喜欢充满未知的、无法进行数学表达的X。在联众国中,一切都是理性的。音乐是按照数学原理完成的,即使人类最原始的欲望—性欲,也要通过理性的方式实现,即“粉红票”。然而,这些都还不够,最重要的是“我们”高超的理性水平已经能够完成剔除“想象力”和“灵魂”的手术。进行过手术的“人”已经成为“像人的机器” [1],面对这种极端的理性像野兽一样肆虐在联众国中是,“我”,D-503已经与其他理性至上的公民不同了。在I-330的影响下,“我”的人性意识开始复苏,“我”内在的感性的“灵魂”被激活,“我”不愿再将“墙里面我自己的世界” [1]赤裸裸地呈现在其他人面前。然而,这场感性与理性的对决以感性的失败而告终,挑战联众国理性的I-330被处决了,“我”也被实施了“伟大的手术”,治愈了灵魂病。作者在结尾,借重新恢复极端理性的D-503之口说出“我坚信我们终将获胜。因为理性必胜” [1]。
《我们》作为反乌托邦小说的最早的优秀典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近似荒诞的未来世界。在高度理性、技术高度发达的联众国中,人们的精神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所有人,作为号码生活在一个人性真空的世界中。
在人性真空的世界中挣扎下载如图片无法显示或论文不完整,请联系qq752018766